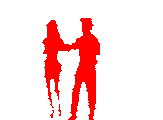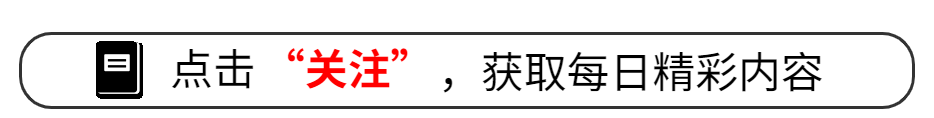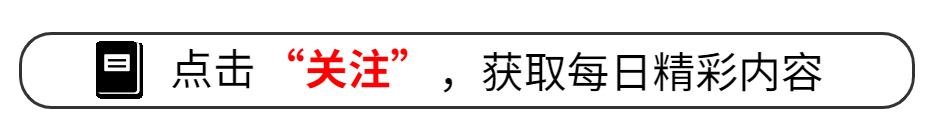从两个问题出发,审视《天桥上的魔术师》中的多元面貌
《天桥上的魔术师》在2021年初首播,片中多以魔幻、不连贯的叙事呈现昔日台北的中华商场。叙事中的故事人物也展现多元和丰富的生命样态:
小巴的特殊爱情倾向、Nori与情人的电话通信,甚至是阿派和朋友们在舞厅的放纵喧闹,都在在印证了解台北中华商场呈现的多元生活样态。

然而,尽管我的观赏经验是毫无疑问地符合现今对于价值多元的观点,身边的亲戚和家人却有相异的看法。他们认为这部剧不符史实,也不符合他们对于当时中华商场的记忆。
身为没有相关记忆的他们,这部剧很显然并不符合他们对于乡土记忆的怀念。这使我省思:难道我对于多元价值观的评价一定是对的吗?还是其实有我并没有发现的面向,会在他们对于怀乡的动机下梳理出一个脉络?

本文从上述两个问题出发,审视《天桥上的魔术师》中的多元面貌。
剧名《天桥上的魔术师》,道出了整部剧的地理位置。而魔术一词,更指出这个地理位置本来就是如魔术般从无到有变出来的。其所呈现的也是观众所期待的想象。剧中呈现客家人经营的锁行、山东人开的包子店、以及书报字画社。

这里呈现的,商业集散地映照出了多元族群生命样态。
《鸣人堂》的一篇评论文章便指出这点,并加以描述关于《天桥上的魔术师》与现下台湾观众的期待。
尽管文章撰写的内容,在标题一开始就设定了故事再现必须符合观众的被动姿态,并预设了一个完整不变的期待,当文章报导原著作者吴明益对于创作的动机时,则话锋一转说明了这部剧「汇聚了从大江南北各地的人人荟萃,天桥上人来人往的身影、嘈杂的人声鼎沸,见证了当时的繁华与时代的缩影」,并说明剧中叙事的虚幻交错,是共同经历中华商场的人「共有记忆」。

很显然,这个纷杂流动的叙事手法,不但充分再现了当时多元的台湾族群的生命样态,同时也与一个共有的观众期待有着复杂的关系。我们如何理解这其中对于观众期待的模宁两可?这到底是纷杂的还是集体共有的记忆?
关于记忆与观众的期待,导演杨雅哲在许多媒体中陈述自身对于中华商场的记忆。
在宝岛与邓惠文的电台访问时,杨雅哲说明了当时火车经过中华商场的风光。并更进一步指出这部剧对于经历中华商场的台湾集体记忆。剧中呈现1980年代正处解严后的台湾。

尽管如此,这个处处充满爱国、伟人传记的社会,仍时时戒备着违反忠贞爱国信条的台湾人民。对于当时共同成长的记忆创伤,访谈人邓惠文很委婉地指出一种「苦涩」的感受。为什么这部描述1980解严后的台湾,并让台湾挤进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开放社会,却让人有股与之相反的感受?
剧中的叙事者小不点在片头一开始便指出如此的记忆矛盾。
剧中他自陈消失记忆的编篡即是存在的意义。这句对着曾帮他画上手表标示时间意义的哥哥直指这整部剧的核心,亦即:记忆藉由他人给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一方面藉由叙事者小不点回忆哥哥Nori的故事,而在另一方面也勾勒了当时的中华商场。

《天桥上的魔术师》刻画了各个族群在台北中华商场勤奋工作的劳动画面。当中不乏四处迁徙的摊贩,而小孩更是家庭劳动的成员。主角小不点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每天放学后,他总要背着一个吊背带四处向天桥上、骑楼下走动或吃饭的路人兜售鞋垫、鞋带。

而在每次工作回家,所得的一切都全数交给妈妈。整个家庭组织的分工犹如组织缜密的公司。家中的劳动和所得分配则交给一个人管理。然而,小不点的妈妈与其他街坊邻居的闲聊,也成为孩子们相互串连、彼此分享消息的重要连接。
这个网络透过街坊邻居相互的事件连系。剧中,菜刀陈的儿子将爸爸的耳朵割下后,逃离了家。这个反抗父亲的事件固然违逆了维系家庭的宗旨,却也指明对于家中父亲的不满。

小不点妈妈与阿盖妈妈在此事件后,便开始相信拜拜有其重要性。小不点和阿盖听闻妈妈们的结论后更将此扩大理解成中华商场的小孩皆要拜拜一说。
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八卦串连却指出了一个无奈事实:尽管父亲被小孩忤逆,事情总有更剧大的原因。祖先的名义固然总有其用处,被忽略或不愿提起的却是父亲被认定的无能。

然而,这个父亲在家中被认为是无能的背后,则是更庞大的威权。剧中,身穿黑色中山装的特务总是在晚上巡查。而在这样有着时时刻刻被监视的宵禁,任何活动都可能被看作违反爱国信念的社会,体制的压迫在剧中是很明显的题旨。
中华商场的地理位置随着1949后迁移来台的各路移民的落居,形成一个商业的集散地。如此纷杂、多元的商业聚落在蒋中正认为肮脏、拥挤下遂整并为中华商场的建设。其所整并的,更是商业集散地的全面体制化。

由当时台湾省官方、警备总部和台北市官方规划的中华商场委员会提供了一个让各路生意人自立其户地开门做生意。然而,没有店面保护的摊贩却总是成了警察驱赶的对象。剧中的魔术师便是鲜明的例子。
而当他在天桥上占到一个位置,并和小不点施展他的魔术时,变魔术的时刻却被前来驱赶的警察打断。这造成故事叙事中,魔幻的断裂和破碎。而对于魔法有着强烈欲望的主角小不点而言,拼贴这些魔术成了很重要的事。用意当然是为了抵抗在威权体制下生活的无奈。

本文试图探讨由主角同是叙事者的小不点一家人,面对纷杂的魔幻和梦想,并借此串连整部剧中呈现的抵抗行动。如果从叙事的内容来看,小不点对于魔术有着相当强烈的欲望。不论是铁环或是小黑纸人,魔术的道具代表着一个远离苦闷生活的出口。当时他对小黑纸人说:
「你们有小黑人专属的学校吗?还是,你们不用上课,只要跳舞」
对于生活的无奈便昭然若揭了。而这句话也另一方面指出对于远离平日苦闷生活的想象,也可以是生活中的实践。这么一来,学校或舞蹈都是魔术可以出现的地方了。小不点在学校向同学、好友们兜售魔术师的道具便是一例。

剧中,小不点兜售魔术的方式是很有技巧的。尽管特莉莎在白纸上写了「大白吃」表示对于魔术的不相信,当这个写不出来的字被小不点用橡皮擦擦出了字迹后,人人称奇。观看的同学随小不点复诵白纸上的字,更是成了赞美魔术的证明。
这里,魔术不仅呈现给观看者称奇的表演,更转化成平日不被相信的事物。
这样的表演方式当然让小不点成了班上众所注目的人。而他的好友们更是鼎力协助小不点的魔术表演。阿盖和阿卡随着小不点到标志着99楼的入口。而阿盖也分享了他在晚上驾驶石狮子游览中华商场的梦境。当阿盖在夜晚的中华商场时,他看到的是家家户户关着房门,小心地度过每日辛勤劳动后的娱乐。

小不点妈妈和邻居妈妈划拳、小佩、大佩和开着书报字画社的父亲,共同讨论复印校刊一事,都在在证明了人民在威权体制压迫下的生命热情。然而,这些家里关起房门的娱乐总是受到威权的挑战。
当有人发现阿盖在办公室外观看后,遂前往阿盖家里拿着照相机威胁阿盖一家人。那操着普通话夹杂着别扭闽南话的特务在一面威胁着阿盖家人的同时,更告诉阿盖照相机的强大力量。

这个展示政权威权,扬言只要他们拍下的画面,皆可能成为消失对象的特务所声明的,当然是从白色恐怖以来延续的国家暴力。在中华商场生活的人民如阿盖一家人,更是在这胁迫下的受害者。
其后的故事发展让我们看到的是,遭受威权暴力迫害下的悲伤故事。当大佩、小佩的父亲为了帮杂志社复印,特务更是在旁监视,甚至协同警察逮捕运书的人和大佩、小佩的父亲。为了烧毁书中被认为是叛乱的内容,大佩、小佩和妈妈焚烧书籍杂志。却也在父亲为了阻挡特务警察不让进门时摔倒,打翻汽油,最终自焚在书店里。

这正是威权胁迫人民而形成的悲剧。
然而,这个一方面控诉着暴力的故事却令人讶异的转往抚慰人心的画面。
当阿盖一家收留在火场幸存的大佩后,阿盖、哥哥阿派和妈妈总会带着大佩在中华商场四处散步、煮中药给她喝甚至在夜晚睡不着觉时唱歌哄她入睡。为的,就是希望大佩不会因为想起家人在火场丧生的画面而拒绝与外界接触。生命的意义似乎成了不确定的状态。

而在魔术师将算命仙的文鸟从活变到死,再让其死而复生后所说的「生老病死,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也给了大佩对于生死的领悟。究竟,人为何而活?整部故事藉由威权的迫害,带出的是一个对于生命的大疑问。藉由阿盖一家人的相互帮助,我们看到的是对于苦难境遇的理解。
而当阿盖对着正要向沿路叫卖水果的菊婶,买着既不甜又不好看水果的妈妈提出疑问时,阿盖妈妈则对他说了句佛教观点:「大家都是辛苦人,可以帮就帮。知道吗?」。这个对于现世苦难的理解,阿盖妈妈藉由帮助菊婶的举动,似乎也影响了她的儿子们。

不论是阿盖与小佩、大佩和小不点平分编篡校刊所得的报酬时,所要求较少一点的钱,或是阿派在面对喜欢的阿猴面前总是给他的宵夜和代替他沿路推销学校制服,对于他人的帮助总是带着妈妈对于他们的叮嘱。
马东就是摇滚李鸿章
《乐队的夏天》第3季都快尾声了,热度很低,肉眼可见的凉下来了。很多人纳闷这是怎么了?我倒觉得这很正常。先说结论,之前的《乐夏》火,不是摇滚行,而是马东行。摇滚的市场本身已经不行了,生生被马东洋务运动了一下,复兴了。马东就是摇滚乐的李鸿章,裱糊匠。我有搞资本的朋友说,中国摇滚本身就不是好项目——过气了,人员还不好管理,这种项目很难搞。娱乐天地2023-10-10 11:47:210000五四青年节快乐!
“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故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李大钊也如是说。青春因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确定自己的目标,追逐自己的梦想,让灵魂,永远栖息在诗意和热爱里。无论岁月怎样改变了容颜,依然,是青年的模样,五四快乐。娱乐天地2023-05-10 14:18:180000毕雯珺成“新晋顶流”?手握多部待播剧来袭,部部爆款相十足
#头条创作挑战赛#近日,古偶网剧《珠玉在侧》举办了开机仪式,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徐璐、毕雯珺这对高颜值CP,更是引发了众人的期待。不得不说,毕雯珺的资源还是不错的,选秀节目出道的他,近几年拿出了不少优质作品,而且目前他手握多部待播剧即将来袭,有望成“新晋顶流”!《墨白》饰演韩京墨这是一部校园偶像题材的作品,改编自超人气言情小说《大神,你家夫人又挂了》。娱乐天地2023-05-27 17:37:320000超模姐姐的5000亿豪门老公,竟是内娱最强恋爱脑?
芒果不愧是芒果,手握十多个综艺大IP,拍一档火一档。最近《爱的修学旅行》和《再见爱人》同时热播,很多人都在通过窥探明星的婚姻细节,内观自己的感情生活。《再见爱人》封神是必然了,从第一季到第三季,它将婚姻里的相互依靠又相互伤害,遗憾和释然,纠结及迷茫体现得淋漓尽致。《爱的修学旅行》刚播两期,从朱丹到周一围,金莎和孙丞潇,到现在最受追捧的何猷君奚梦瑶,也算是呈现了婚姻的多种样本。娱乐天地2023-11-21 16:24:280000《繁花》中9位神仙配角,网友:半个娱乐圈的人都来客串了吧?
文|小雨淅淅编辑|司徒夜信息源:本文陈述所有内容皆有可靠信息,来源赘述在文章结尾《繁花》作为王家卫呕心沥血了三年才完成的一部作品。一经播出,就迎来了现象级的大爆。剧中的主创们,也是一个比一个地惊艳。就连王晶导演都说这是家卫兄的又一杰作。甚至还表示看到胡歌让他想起了全盛时期的周润发。不得不说,这个评价,称得上是高赞了。而唐嫣,也被王晶夸赞道“大幅进步”。娱乐天地2024-01-09 10:16:05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