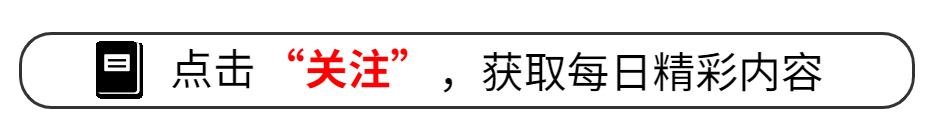电影中的人设重要吗?从《不爱钢琴师》到《浪游》,重新给出答案

在电影这个行业中,专门有一个课程叫做「电影叙事方法」。老师说:
“每个人都是故事。「人物」是故事的核心元素,一切情节的旋扭与绞缠,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然而我向来对这个观点抱持怀疑。若你要述说一个故事,人物永远无法是一个足够饱和的原点;而其他事物,譬如风景、路线、特定氛围,亦可能成为叙事中更重要的主题。但我不否认,人物作为故事书写的开端有着悠久传统,而所谓的「人设」,就是作者必须执行的第一件工作。

厘清人物的个性与行为模式,安排身份背景,赋予样貌和形象,如同介绍一个朋友般将其介绍给读者──虚构内容的具体化及合理化,掀开入戏的帘幕。
入戏是必经之路,因为人类天生渴望听故事。

好的人设,能更有效地引导观者产生移情作用,投射自我于角色,逸离现实人生的条条框框。坏的人设,则让人无可避免地意识到剧本的技术问题,落下一抹目睹魔法失效的冷淡神情。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优异人设,莫过于《不爱钢琴师》的主角拉娜。

她是一个为了婚姻与家庭、放弃钢琴家前程的女人,她致力于让儿子成为顶尖钢琴手,却造成难以冰释的母子心结。在电影中,已届暮年的拉娜散发出一种严厉、强硬、不可亲近的气息,她压迫、控制周遭的人包括自己,对未能拥有的成就心怀怨恨,认为世界欠她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
若仅依上述所言,这似乎是一个负面人物,但当我观看这部电影时,却深深被她那锈刀般的模样吸引,且能共情。

或许关键在于电影以相当细致的手法呈现拉娜内心的苦涩。
这份苦涩,让她无法以平衡公允的姿态与人相处,总是摆出一副锋利的高姿态来自我防卫;也让她无法全然真诚地为举办独奏会的儿子感到骄傲,而掺杂异样的妒意。其实拉娜早已疲倦,她想放下遗憾,接纳既有的生活,却在环视孤冷居室的过程中,屡屡望向那个适合一跃而下的窗口,还有原来摆置钢琴的一面空墙。悔恨的母亲、与成功失之交臂的女性??

这个人设并不创新,《不爱钢琴师》照样将其处理得极具魅力,角色宛如血肉之躯,在我面前紧绷而难熬地行走,她的心痕,在岁月中拖出一条长长的擦伤。
因此,我认为「预备型人设」其实不足以启动人物的诸多幽微面向,藉由细节的持续堆叠,观众才能真正落入角色生命的深邃漩涡。
譬如拉娜在整部电影中穿着高级质感的服饰,流露精心打扮的品味,这也许可以暗示她的经济位阶,但最重要的还是她选购晚会小礼服的一幕:拉娜的表情微微显露出一种缺乏自信却仍想争强好胜的态度。人设只是草稿,人物必须在环境中、在情节里,才能爆发特质。

作为延伸,我试图更跳脱地来思考人设:是否有所谓「反人设」的电影?也就是说,没有名字、没有背景、形象模糊、不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的角色,主导了整个叙事,以至于它所处的位置,能够持续撼动着虚构之境的边界。

我率先想到的不是电影,而是玛格丽特.莒哈丝的小说《劳儿之劫》,故事中的劳儿比起一个「人物」,更像一座载满回音的暗影城镇,吸纳清晰具逻辑性的叙事与阅读意识,将之化为乌有。你会因为那种破碎,对眼前这个浮字而生的世界产生质疑:「劳儿」究竟是一条散逸的基准线,或其实是最为精密的建构?
波兰斯基就读洛兹电影学校时期所拍摄的一部短片衣柜流浪记,关于两个无名无姓的男人,游走小镇推销一座从海滩上捡到的衣柜,他们从水里冒出,最后亦消失于浪花间。我认为这部电影说的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奇异降临,人物如同空白帆布,他们所行经的事件则如油彩,彼此碰撞、蹦跳纷杂意念,为故事带来开阔空间和趣味盎然的诗意。

布莱希特所提出的「疏离」剧场理论,意欲阻断观众对于剧中人物的共鸣和投射,拔除俨然舞台的致幻剂,让观众从沉溺故事的被动接收者,转为有能力思考虚实边界与扮演之术的「核心角色」,进而达到改革社会现状的目的。
戏剧并非真实,将戏剧经验带入生活的观察里并做出行动,才能使其真实。而「疏离效果」的其中一个重要方法,即是反向展示角色的「被扮演」状态──贾克.希维特的《莎莲与茱莉浪游记》是一个相当丰富的例子。

这部电影的情节大致是关于两个少女的日常游戏,她们吃下一颗魔法糖果之后,可以潜入一出在豪宅里永恒轮回的家庭悲剧,药效结束后随即晕眩苏醒。
首先必须谈到的是,《浪游》一片即兴跳跃的叙事语法以及童趣风格,来自两位演员Dominique Labourier、Juliet Berto和导演彼此激荡的突发奇想,也就是说,莎莲与茱莉的人设含有「进行式」的时态,在拍摄过程中拥有异变和成长的动能。

电影本身则有着层层剖析的意趣:莎莲和茱莉多次进出剧中剧,干扰了豪宅内部的「完成式」故事并改变其结局,也介入了彼此的人生,互相玩起「角色扮演」的游戏。例如交换衣服与情人,莎莲假装自己是茱莉和她的青梅竹马见面、茱莉代班莎莲的夜店魔术秀工作??到了电影最后,甚至反转了整个故事的起手式:
原本是茱莉在大街上偶遇莎莲并悄悄尾随她,忽然变成是莎莲尾随茱莉──她们还原为素不相识的状态,前面两个多小时的情节堆叠仿佛全数删除,而有个全新的剧本正蠢蠢欲动。

《浪游》狂野地运用上述后设手法,让电影遍布破格之口,观众随时有可能掉出「外面」而产生某种近似疏离效果的距离感。那颗魔法糖果象征入戏的咒术,你与两个少女一同踏进幻域,却看见死白冰冷的人物上演着无限重复的、命定式的中产阶级荒谬剧,似乎颇有对于传统舞台和电影叙事观的讽刺。
藉由这些角色的暧昧定位,我清晰觉察到「看戏」所带来的着魔:我如何沦陷与退潮,潜入一个淋漓尽致的梦又再度转醒。

电影中的人设重要吗?从《不爱钢琴师》到《浪游》,重新给出答案。而这个答案,好似又不唯一。
事实上,「反人设」指的不是「无人设」,而是人物比起作为被观看对象和叙事主体,可以是更有机的存在:生发情节,延伸感触,提示虚构的边界。这种极为特殊的人设,其生灭无来由亦无终端,他们的样貌如水不可勾勒,他们的身份不明确且易于解构和流动,他们就是浪游者,而他们的名──非常名。

此时,我想起安妮.华达的《短角情事》,一对在真空的时光里行走的男女,他们究竟是谁?我无法认识他们的过去和未来,只能轻轻抚触搁浅的现在。然而,当他们漫无目的地走远,我似乎可以跟着去到任何地方。
何超欣近况曝光,跟奚梦瑶同框不化妆,裤子宽松手臂肥大也不焦虑
何超欣:自信的典范,不拘小节的独立风采在娱乐圈这个大染缸中,何超欣以她独特的魅力和态度展现了新一代女性的自信与独立。她不仅是赫赫有名的澳门博彩大亨何鸿燊之女,更是一个在公众面前敢于展现真实自我、坚持己见的年轻女性。娱乐天地2023-11-14 12:19:020000“单眼皮女神”吴倩莲:告别庹宗华,嫁给普通丈夫,低调恩爱16年
#冬日生活打卡季#偶然间看见叶倩莲的照片,不禁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她出生在台湾的一个中产家庭。或许是因为女孩子的自尊,在小时候被人说“丑”的时候,她总会用自己的叛逆来掩饰自己的脆弱。这种环境下成长出来的她,让她天生比别人多了一副“反骨”。依靠着这身“反骨”,她在面对未来的逆境时,始终坚强直面困境。她的星途很顺利。娱乐天地2023-12-11 18:50:520000又一位美女主播嫁人了!老公是圈外富商,金星给她当证婚人
近日,又一位美女主播嫁人了。原来安徽卫视的当家花旦余声结婚了。她的婚礼很热闹,也很浪漫。金星、周群等人都有参加余声的婚礼。金星还当了婚礼的证婚人。据报道,余声和她的老公在步入婚姻殿堂前,已经相恋多年了。娱乐天地2023-06-08 12:05:170000围绕《小鞋子》展开的电影剧情,通过5方面细节深化主题
《小鞋子》这部影片通过两个孩子与一双鞋子的故事,从孩子的视角来展现儿童的纯真和平凡生活中的真、善、美,极具人文主义色彩。伊朗最为普通的家庭生活如同万花筒,折射出伊朗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环境,尽管镜头下的伊朗平民生活在物质匮乏的环境下,却依然能够保持宽容仁爱的本色,这也是马基德的作品总能打动人心的原因。围绕《小鞋子》展开的电影剧情,通过5方面细节深化主题.娱乐天地2023-05-07 21:09:440000中国美女千千万哈尔滨要占一半 来看黑龙江籍顶级貌美长腿女星
#记录我的2024#最近哈尔滨可谓是旅游胜地一波波的南方土豆蜂拥而去还有“小砂糖橘”、“小菌子”等东北人民的善良和好客美景让人看不够,流连忘返其实,这里的美女更是成群如云说实话不盘点不知道一盘点真让人吓一跳黑龙江的美女真的占了娱乐圈半壁江山关键还个个美的极其鲜明有特色[爱慕]都说神仙姐姐其实她妈妈颜值更高刘亦菲的妈妈叫做刘晓莉1959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娱乐天地2024-01-10 12:21:55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