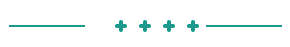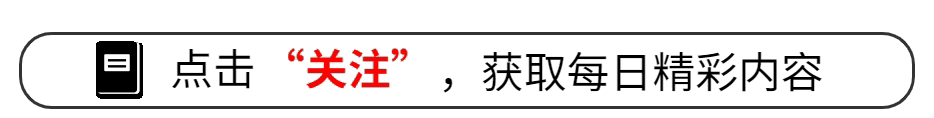藉由弗洛伊德的生命,审视《当世界不再下雪》中神秘男子的观点

影集《弗洛伊德》以弗洛伊德1890年代于维也纳医院实习的经历作为故事背景。此时的弗洛伊德,尚未透过《梦的解析》在心理学界掀起争议与风波。
剧中,一位个案兼灵媒的神秘女子莎乐美,介入并扰乱弗洛伊德的生理及精神生活。然而尽管莎乐美于历史上真有其人,真实的莎乐美仅与弗洛伊德建立「单纯的」友谊,成为弗洛伊德思想的信徒,并无如《弗洛伊德》中的莎乐美与弗洛伊德建立悖德的关系。但是,我们仍需对真实的莎乐美与弗洛伊德的实际相处情形保持怀疑:

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必须怀疑弗洛伊德与莎乐美之间发展了如后者分别与尼采和里尔克之间的情爱,而是我们必须怀疑莎乐美对于弗洛伊德的心灵富足,是否仅有「单纯的」情谊意义。

如《佛洛伊德》的结尾,维也纳为了掩盖莎乐美所造成的不安与动乱,要求弗洛伊德烧毁那本关于莎乐美的书。在最后一次与莎乐美的会面中,弗洛伊德向莎乐美传达了自己烧掉著作的失望与落寞。对此,莎乐美答道:
不要写一本书关于我的书;请为了我,写许多本书吧。
此处,我们总算可以将虚构中的莎乐美,以及真实的莎乐美相互连接:两人对于弗洛伊德──不论是影集中的,或是精神分析史上的──和其他思想家而言,无疑都是不可或缺的缪思。她们的存在迫使他们去追寻和理解许多看似无解的事情。

于是,我们或许可以藉由弗洛伊德的生命,审视《当世界不再下雪》中神秘男子的观点!
对于按摩师泽尼亚,除了他出身自曾经遭到核爆遗害影响至今的切尔诺贝利小镇,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他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从黑夜走到白日,再从白天进入漫无止尽的黑夜里,而他走过的城镇也仿佛四季不见阳光,黑夜与白昼,时间与空间,彼此融合成单一、永恒不变的「一点」。

然而,当我们看见一幅挂在泽尼亚住所墙上的风景画时,我们随着泽尼亚对这幅画的凝视,一同被吸进了画中:画中的草地开始随风拂动,一位背对着镜头的女人坐在篱笆上,抽烟望向远方,远方的天际映照着傍晚的彩霞。
这一幕不可能不使我们联想到塔可夫斯基的半自传电影《镜子》的第一颗镜头,正是饰演塔可夫斯基母亲的捷列霍娃坐在围篱上,望着远方,等待着丈夫的归来。

即使这一幕──观看自己母亲的视角,自己与母亲之间的关系,自己眼中的母亲与他人的关系──对塔可夫斯基而言,或许是极为个人、也极为私密的,然而塔可夫斯基意图透过这个画面所传达的,并非记忆里母亲确切的模样。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个动作,而是透过对于母亲的重建,来追忆自己的母亲,追忆自己对母亲的情感。
于是,从此看来,泽尼亚在墙上的画中所看到的母亲,以及其他记忆片段里所看到的母亲,即使与塔可夫斯基的母亲是相近的,甚至完全相同。然而这些画面对于泽尼亚而言,仅是他对于母亲的一种想象,以及情感的溯洄。

泽尼亚在小镇法语学校的期末发表会上突然消失之后,我们看见许多挂在学校墙上的儿童画作,而这些画作的共通点,皆是他们记忆里泽尼亚的最后身影:身着滑稽表演服的泽尼亚,为母亲们按摩的泽尼亚,甚至是如超人般翱翔天际的泽尼亚……
「你必须成为一位英雄,才能拯救别人。」
泽尼亚的母亲在临死前,曾如是对他说道。然而,当这句话再次浮现于泽尼亚脑海时,母亲早已失去了气息,动也不动地躺在棺材中。泽尼亚俯身下去,亲吻了母亲,作为对母亲最后的道别。直到此刻,我们或许终于能够明白:使泽尼亚成为「按摩师」、使弗洛伊德成为心灵黑暗大陆──特别是女性的,因为佛氏的个案多为女性、以及使塔可夫斯基进入图像创作的缘由,彼此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自身生命的历程,某种程度启发了他们在探索人类心灵过程中的灵感──现实中的弗洛伊德因为年轻的继母而开启了对于恋母情结的构想,进而发展出一系列庞大的、精神分析的系统。

虚构的弗洛伊德基于与莎乐美的奇幻经历,开始将自身所经验的一切,付诸于探究神话、仪式与原始欲望之间的关联;至于泽尼亚,则是基于母亲最后托付与他的遗言,而开始在按摩的过程中──更精确来说,是与众多女性及少数男性客人的关系中──寻找他与母亲之间的联系。
然而,藉由按摩/催眠治疗/谈话治疗进入女性的想法,也就是她们的潜意识里,透过发生关系来治疗她们,在我们眼里看来是荒谬无比的。

就如同对于弗洛伊德将所有的心理问题归咎于欲求不满足,将所有的冲突简化为父亲、母亲与主体之间的三角关系,在没有自身相关经验的情形下,我们感到嗤之以鼻一般,甚至认为这一切仅是弗洛伊德对年轻母亲的「幻想」而不足挂齿。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这个具有庞大体系的「幻想」,除了荒谬之外,其所隐含的另一个意义便是一种不可能性:基于否认欲望为造成自身心理问题的根源,问题的本质是荒诞,也是不可能发生的。

如同泽尼亚介绍自己来自切尔诺贝利──理论上,切尔诺贝利事件爆发后,该地已有近十余年的时间无法居住,更何况泽尼亚出生于切尔诺贝利事件后的七年内──,开头向劳工局的局长说道「我会所有的语言」,不留一丝痕迹地消失在世界上,却仍以英雄的姿态出现在孩子们的画作上。这一切暗示着某种人类不愿意面对,并且试图透过将之定调为「可笑」来逃避面对的问题。
这也正是《当世界不再下雪》结局黑画面上所显示的:
“2025年,世界将降下最后一场雪。”

不清楚泽尼亚离开小镇多少时日后,小镇下起了雪。只是,这场雪,如同电影中身份不明的叙述者所言「掉落的雪像灰烬一般」,以及联合公园的歌词「灰烬如雪花般飘落」,核爆之后无数的放射性尘埃被释放到空气之中,随着雨水或雪降下──此时,尘埃的确如雪花般飘落。
只是,这句话并非真的以气候变迁的角度,指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予取予求,将会带来严重的自然灾害,而是一种对于人类末世的预言。就如弗洛伊德晚年对于二战的爆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他早已认为理智与文明永远无法战胜人类的毁灭本能,而等在个人前头的死亡,人类所迎向的灭亡,是我们不愿面对的事实,却也是确凿地戊限在我们眼前的命运。

但是,若一切的心理问题,皆如弗洛伊德所认为,源自于「欲望」或「驱力」,那么作为一名治疗师,泽尼亚的无故消失似乎便预示着心灵治疗的不可能性。当他的出现短暂地抚慰了小镇上众多的寂寞心灵时,他与这些人所建立的关系,证实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可是他的消失,也意味着原先已经被解决的问题将因为泽尼亚的不在而再度浮上台面。人们将永无止尽继续等待着下一个泽尼亚的出现。

总体而言,对于泽尼亚自身,他所施行的治疗能够建立他与母亲的连接,而对于被泽尼亚治疗的人们,他们所接受的治疗终究是不可能的──这对应到弗洛伊德临终时对于当前人类自相残杀的处境毫不感到惊讶的态度,也显示了一种极端的悲观主义:不论是泽尼亚或是曾经被他拯救的人们,即使我们有生之年能够看清楚自身的问题,它们仍旧是不可能被治愈的。
春晚一句台词识破潜伏间谍,去世23年的赵丽蓉,仍被官媒发文缅怀
1996年的春晚,赵丽蓉老师表演的一段小品,瞬间火遍大江南北,她的名气也跟着随之上涨。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这小品里边的一句台词,在未来某一天,竟然会直接识破潜伏间谍。警方对于这样的事情也是无比的震惊,自己想方设法想要解决的难题,竟然直接被赵丽蓉老师的一个小品给解开了。现在来看的话,赵丽蓉老师已经离开人世23年,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官媒没有忘记她。娱乐天地2023-12-28 12:19:000000悲剧!《大宅门》导演郭宝昌离世,竟是因为一次意外摔倒!
10月14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出:《大宅门》导演郭宝昌的丧事已经办理完毕。这位传奇导演原本计划在10月2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推出一部高达60万字的巨制小说《大宅门》。各界朋友们早已做好了参加活动的准备,然而几天前,郭宝昌的人生轻轻地被一次不小心的跌倒推向了终点站。娱乐天地2023-10-17 02:35:010001《且试天下》终于定档了!神仙选角阵容吸睛,不愧是古言天花板
近日,古装爱情武侠剧《且试天下》官宣定档的好消息,吸引了无数人的围观,在众人殷切地期盼下,终于见到了曙光。该剧未播先火,早在开拍之初,在网上的热度就居高不下,由同名小说改编而来,讲述的是俊雅少年丰兰息与娇艳公主白风夕携手闯荡江湖的武侠爱情传奇故事。娱乐天地2023-05-29 08:29:560000嘴对嘴亲吻,当众强吻30岁女儿,没边界感的明星父母有多离谱?
文|美妙的探所编辑|美妙的探所“三观炸裂!”30岁女儿竟被老爸当众嘴对嘴“亲吻”,三更半夜公开给女儿写“情书”。这种种令人发指的案例,究竟是亲情的体现还是道德的沦丧。本来“女儿是父亲的小情人”仅仅只是一句“俏皮话”,但是却被这些明星硬生生的搞成了“事实”。“人类的退化,兽性的显现”在这些明星的身上体现到淋漓尽致!娱乐天地2023-09-17 12:14:360000“看狗都深情”的4位男演员,个个生了一双桃花眼,天生就带苏感
文|娱乐联盟官编辑|娱乐联盟官电视剧中,常常看到男女主角对视的时候眼神都在拉丝,不过一双漂亮的眼睛的确可以让对方更快入戏。而且对于演员来说,眼睛好看,颜值更是加分不少。女生的眼睛要深邃,仿佛让人可以看到星空,男生的眼睛要深情,因为这样才能拨动女主的心。就像娱乐圈这几位男演员,他们的眼睛很迷人,那深情的模样,谁看了都马上沦陷。娱乐天地2023-07-28 11:07:5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