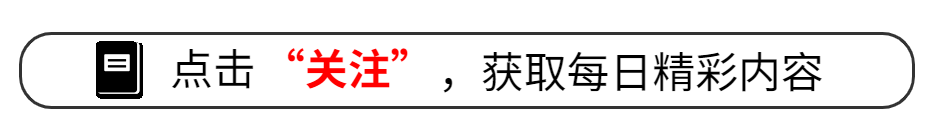通过导演的多部影片风格,审视这其中的共性和特殊之处
要谈《沙丘》电影,我不大想从赫伯特的小说谈起,考察故事增减,更多时候只是盘点工作,费时却不劳心,倒想先回到魁北克导演维勒纳夫转战好莱坞后一系列风格操练的原点。尤其是2013年的《囚徒》(即《私法争锋》),与2015年的《怒火边界》。

维勒纳夫拍摄《沙丘》前的几部英语片,最重要的象应是「迷途」──这里的「象」并非人象物象,而是自有形物质排列方式中生成的无形迷失感。
表征此象的方法,可简单地概括为一种极简主义,亦即二元用色(大片闷盖的单色对比鲜亮的局部色彩)、摄像机运动简化(无论摇镜、追拍皆点到为止,或干脆不动,改用移焦)、用剪辑严密控制景别次序、调度多以视线遮复为目的,并导入大量旁跳镜头。

这创造出一个个自空间层次渗出敌意的舞台:黄沙、落雪、烟雾、隔窗、頹墙与意义暧昧的旁跳被摄物既是自然世界隔绝人物的手段,又像人物自我的防卫机制,一种「你只认得出自己、也只剩自己能认识」的寂寞身份迷宫。
理所当然地,这些电影无一例外有悬疑剧色彩。但类型片应许观众的情节张力又在嶙峋的视觉操作下被剥削出无机感,远不比人物深陷的身份风暴来得真实。

维勒纳夫电影的演进是个有趣案例,因为较之其他工作者,他是到进入好莱坞的声色名利场才真正摸索出风格,产出的作品愈来愈慢、愈藏愈多,而且愈见其严慎。这终成一家之言的「藏」,没被私密事绑架,而是表现力强、题材弹性高却又带破坏性的方法,适于为类型片叙事注入幽闭感和抑制情绪。
通过导演的多部影片风格,审视这其中的共性和特殊之处。
他在加拿大摄制的法语片要活泼得多,有临摹新浪潮导演高达的爱情喜剧(《8月32号在地球》)、砧板鱼肉成精鼓簧的科幻剧(《迷情漩涡》),但这些视觉实验的表现欲大都压倒了原生性与创意;而《烈火焚身》乍看扬名国际,却免不了三观过正的症头。

维勒纳夫野心宏大,想自古时的《伊底帕斯王》与现代的移民离散情状间,炼制出两种人伦悲剧的同形,调度却平平无建树,倒是仰赖悬疑快感操作、Radiohead金曲、大绛红字卡等机关,要说召出天地不仁的生命即景,也是机巧与猎奇过头,未免太便宜古希腊戏剧了,还更似当代影展机制下一次性的可抛式人道主义情感兴奋剂(拍完《暴雨将至》即成江郎的米丘曼夫斯基,便是一例)。

此时期真正显露维勒纳夫图像才华的,应是2009年的《蒙特娄校园屠杀事件簿》。
以1989年的工程学院大屠杀事件为蓝本,竟是在校园枪击、女性主义、社会案件的三重耸动前提下,维勒纳夫斗胆隐去因果分析,略显陷溺地以其往后英语片形式主义的优腕劣足,自数个案件当事人交错的生命史勾画出暗涌着暴力的孤冷情调,叫人隐隐不安。

稀薄的故事、黑白摄影下个个孤绝的道德小宇宙、落雪枯树凛风、幽闭的车与房与窗、排列秩序井然的远景建筑群像与天花板灯、富象征意味的旁跳物,尤其缓缓移向墙面《格尔尼卡》的观点镜,在模糊的故事中开启了与抽象画的冷酷形式互文,像是为片中屠杀场景凸显的无机感(而非论文纪录片的增知性)。不只情绪疏离,还包含被展示却不被解释的事件因果链──奠定孤立的知性刺点。
无论是否苟同电影对暴力成因悬而不断,也姑且不谈援引抽象画解释历史事件(而不是倒过来)是否只是狡诈地自一个谜遁入另一个谜中,在《蒙特娄校园屠杀事件簿》,维勒那夫至少拍出了一部美丽(且空洞,或许)的电影。

要说还孤峭得不够且略显矛盾的,便是镜头运动过于直观地充当起图像的情绪破口,大量的长时间推轨、手持摄影与稳定器拍摄在《蒙》中交叉使用,但这拍出的丰富镜头动线、角度变化(甚至单个长镜内出现180度的上下倒转),在往后的维勒纳夫电影几不复见。
情绪释放感最显著的无疑是尾声那颗推轨镜:幸存者决意为尚未出世的女儿重拾希望,紧接着的推轨镜用单点透视拍学校长廊,但角度有些古怪。原来,镜头是上下倒转地顺着天花板推向深锁的教室大门,仿佛宣告要以母性力量回击长廊的血腥历史。

来到好莱坞的维勒纳夫,其调度究竟受摄影师罗杰狄金斯影响多深,终有非外人道的成分,但狄金斯与维勒纳夫几次合作的成果,足堪自傲。以这套极简风格拍人迷路,一切对银屏外的人来说细节太清、层次太明,显得画内行者皆在黑巷里摸路。迷途之象,并非凝滞不前,它必须是有目的的运动过程,只是走着走着却丢失了标的。

《囚徒》的雨夜驰车、《怒火边界》的边境军旅因此皆成绝佳的视听演示,足以让维勒纳夫证明自己有好莱坞同行缺失的洞见。此刻,不细谈夹在两片间的《双面危敌》,并不因为此片晦涩,而因为它恰是最清楚的维勒纳夫电影。
如同维勒那夫自己所说:当《双面危敌》被限制在表征主角的心理问题,整部电影的视觉不过就是捕捉一个历史教授的身份认同在驯羊性格与兽性欲望间摇荡,没有再多了。
《囚徒》与《怒火边界》的塑型难度相较更高,因为维勒纳夫被迫走出人物的心灵暗箱,不再有空间以潜意识或心理分析为借口玩视觉象征游戏,而得实打实地自狄金斯镜头下没半分虚矫的自然光景中杀出风格血径。

《怒火边界》拍车队入境,极大远景航拍追踪车队、远景呈现车外物件、车内人物只拍特写,三种景别错落,并以一个极简明的纪律做统整:节制任何改变景镜间距的镜头运动,尤其不让物件景别在单镜内巨幅变化。
更细致点说,一个景别几乎只同一种观看方式绑定──举例,要表征车内特写的对象看向车外,则若正拍特写对象窥视窗外的动作,观点镜头一定以窗景表现,而不能越过窗面直接拍窗外事物。

前述中近景别的操作,是搭配直线等速前行的航拍远景,缺乏环型动线。镜头远过一个限度,画面物件的立体感便被压缩、细节便被省略,再更远一些,便滤(律)得赤条到仅剩线与颜色,得以自三维空间构造二维图象(库柏力克《鬼店》拍远景酒店迷宫的方法,堪可对照),竟能将边地莽城拍成高垒深堑的人造环形迷宫图。
维勒纳夫酷爱的环形迷宫图,其二维图形可拆解为数个大小不一、圈子某处裂了口的同心环。《怒》表征迷宫图景时,以有形荒城为经,抽象剪法为纬。

就后者而言,再度以航拍远景为例,可发现《怒》不用镜头的连续运动创造远景层次,而是让镜头在单一景别内等速前进后,直接剪到下一个景别更小的等速镜头。剪辑在此即是破口──每次带有景别变化意义的剪接,都成了闯入另一层同心环的「非法入境」,直接改变观众与迷宫内核的距离关系。
这严苛景别纪律型塑出的画面关系,说来像是递归函数或数学归纳法,或一层层一包一的俄罗斯套娃、鱼中鱼,将单一时空连续体的远中近切线切得明白干净,能勾引观众联想幽闭或隔离,从而生出利落的叙事劲道。

尤其是数次衬底的视觉跨界──如一次移焦前,观众耳闻远方枪火闷雷般作响,墙上糊糊的失踪妇孺海报霎地锐化如电,或官兵旅途中数次管窥临车(其实就是拍偷窥,但因为双方皆在车上,故有调度上的用心),最后将一路走来皆像保命符象征的车做成他人血牢。
我们甚至能明白论证,这样的划界为景别附上施加道德观点的功能:军旅终点那场枪战,只有留在车内的女探员是用特写拍完且是拍她被动地举枪自卫,下车「出界」的探员们因为主动迎战劫匪,自然就不被这特写镜头的道德律绑住,而能以别的景别框限之。

《怒火边界》将迷途之象施行于好莱坞资源撑得起的空间奇状,早了两年的《囚徒》则利用纸绘、雾气、光晕、雨点、落雪、水痕等小而美的点缀媒材,说了一个「视而不见」的迷路故事。

《囚徒》作为风格原点,不如《怒》之处无非是意象流于惨白,因为那张关键的环形迷宫图,将之于远景层别的空间可视化的方法尚未于《囚徒》发展出来,只好最不藏锋地在此片降格成露骨的象征物(作为后来《怒》远景方法的替代品)。
剧中警探循线东查西访,竟还真找到一个嫌疑犯酷爱在地图上填绘迷宫,还画得分外有条理,惹人发噱──借(自然的)景作(心灵的)画,前者可视却不清楚,后者不可视却叫人深陷,这当然讲清故事题旨的里外,却为观众架了不必要的理解捷径。

《囚徒》的重头戏仍是将具视线干扰作用的小物件有目的地置入调度中。尤其尾声那段飞车,说来就是拍「警察送受害者就医」,也没用特技演出催逼你心脏,却一口气提炼出了全戏最好的一段明流暗涌。霏霏雨雪、蒙蒙水雾、萦萦光晕??
电影早先前使用过的视觉遮障,此刻通通顺应警车加到最速的动感在黑夜中荡漾起来(理所当然使人想到黑泽明),就连驾驶特写/车窗观点镜头的密集正反拍也有巧思,因为警车快到达目的地前,驾驶看车窗的观点镜头其景别本来固定。

直到配乐声倏地收小,才接连出现两个景别有异的观点镜头──都是由车内往外拍的车窗特写,但一次比一次靠近车窗玻璃,最后一次特写贴车窗贴到了极处,水痕几乎将所有荡漾的视觉遮障凝成一团,已经看不清前路了,此时镜头切回驾驶,再一次反拍时,观众方知道雾最深处亦是迷途尽头:车窗外的急诊室灯箱就在眼前。
我们不得不说,《怒火边界》这片名可能比原文的《刺客》更佳,而《私法争锋》相较于直译的《囚徒》是劣译,皆因为其图像对「划界」的联翩浮想。

我们若选择只谈物理的分界、情感的分界、权势的分界、道德的分界,都要与其失之交臂。
换个角度说,自《怒火边界》后,维勒纳夫的「慢」之所以棉里裹电。正是因为这影格与影格远近追放间的裂罅,都蓄满了故事要旨的各种微型版本,像,若看完整出戏再检视《怒》的边境军旅段落,害怕被爆雷者「雷残」的观众应该要惶惶不安,因为它根本是全片的微缩模型,连人物关系也交代完了。

回溯性地检视《怒》与《囚》(或卡在两片间的《双面危敌》),它们违反通俗电影处,正在于故事的时间演进好像没明显的生成力,反而是将前述的军旅戏、迷宫图的构成方法循环利用到极致。这个方法在《怒》完熟,因为若列举《怒》的好戏,袭击毒贩隧道、开场惊见朽墙藏尸等等皆有可观,但你似乎只选一场戏来谈就能宏观道尽整部电影。

若说维勒纳夫有什么真正以全片时长为幅度来创造的,就是将具有意象统摄作用的归纳法原型(或说,所谓归纳法的)拖延到片长再浮夸的电影都得有的尽头才说明清楚(环形迷宫的最外圈,终究也得是环形)。
类型片来到二十一世纪,维勒那夫电影自然不会省去必备的故事真相或解密底牌,但其图像趣味之生产,却是反复自复多中淘汰常人毕生难易的行为与思考模式,好将人物与充满敌意的外在环境区隔开来。

因此观众(打呵欠或狂喜)的恍然时刻、电影(变好看或无聊)的疯魔时分,便是那些人工感些微过头的视觉glitch徐徐堆叠至特定限度,「一切情节皆是虚设的幌子与机关」与「单一意旨之反复点缀、回弹与折射才是实像」两点终于交集。
你以为每个人的故事都值得花一生说完,他三言两语偷偷道尽,还重说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非要不信邪的你相信原来有些迷路的人注定出不来,而一部当代类型片还可以不发展人物、不解决问题,只是拍人物一次又一次地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拍完《怒火边界》不久,维勒纳夫便转战梦寐多年的高成本科幻电影,但尚能保持前述的可贵质量,《银翼杀手2049》那场诡魅的戏便是明证。
来到二十一世纪,人们已习惯那些借用视觉「换皮」的数位扮演游戏,然而维勒纳夫选用带毛边的投影来缝合叠像,而不是使用让皮相与肉身无缝贴合的视觉技术(好比绿幕),正好体现了他对人物孤立状态的敏感。

多重曝光一类的后制成像能创造类似视效,但多重曝光技术隐含幽微的虚实分界:我们多少能察觉,被叠加物件的视觉叠加状态是后设层次的抽象信息,适于表明创作者经手的外在痕迹,却不利于在虚构世界内部构造人物对叠像视觉的情感。
叠像瑕疵显示乔伊拟像无法完美依附于j女的身体运动,就好像K的欲望投射原来不指向j女,于是拟像与其依附物间不时发生的行动分离,也就成了K无形欲望的有形裂口。所有将这场戏诠释成AI女友乔伊与K透过一场戏显露「非人也有真人性」的人,无疑都忘了乔伊始终是设计来顺应K的欲望的程序。

《烈火焚身》图像品味有限,但它作为维勒纳夫往后重复利用的故事原型,却又有趣,因为串起这些迷途之象的故事肌理,正是一个个伊底帕斯悲剧的变体。「喜欢伊底帕斯」几近艺文陈腔,但维勒纳夫自《烈火焚身》后每部英语片都是伊底帕斯,这就让人不得不将之视作他的执念。维勒纳夫在伊底帕斯的故事里看到什么,十分可疑。

就我当前的看法,维勒纳夫并不真像近年崭露头角的尤格兰西默一般有重述希腊剧作,他似乎只是展示伊底帕斯框架作为一种复写意象的视觉装置的可能性,而闪回、闪前、梦境等元素,他常信手借来巧用一番,却又显得无比稀薄,终归是类型文本的方便法门。
九寨沟地震后,第一个捐款的明星为何是黄晓明?难怪baby那么爱他!
2017年8月8日,晚9时19分,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附近(北纬33.20度,东经103.88度)发生了6.5级左右地震。地震一发生,消息迅速传开,很多明星纷纷为四川震区祈福。黄晓明发微博为震区祈福。黄晓明的明天爱心基金会第一时间为灾区捐款50万元,用于救灾、灾后重建,并且连夜向灾区发放物资。明天爱心基金会的当地志愿者,也以最快的速度加入到了救组行动中。下面我们就来回顾下黄晓明行善:娱乐天地2023-05-26 04:00:220000解读《蜘蛛人:无家日》中的剧情和人物设定,相比前集有何不同?
《蜘蛛人:无家日》绝对是漫威/索尼今年最具话题性的电影,从宣传就跟观众玩着心照不宣的游戏。「谁可能会出现?」的讨论或许该反过来说:「谁可以不出现?」毕竟面临的反派是如此之多,涉及的危机是如此之大,整个宇宙都要被撕裂,复仇者联盟还不来处理吗?一只社区型小蜘蛛要怎么处理这么大的事?疑问驱使观众进院。娱乐天地2023-05-08 12:33:220000她被称“韩版杉菜”,凭美貌进入演艺圈,如今34岁发胖变成这样?
前几天举行的第22届富川国际奇幻电影节上,一位韩国女星意外的上了热搜。而她上热搜并不是凭借新作品或是她走红毯时的美丽造型,而是因为她发福了,跟当年的清纯形象相去甚远。这位女星就是被称为“韩版杉菜”的具惠善。娱乐天地2023-05-31 00:59:4600005位因逃漏税毁事业的明星,罚款坐牢被起外号,没有一位是无辜的
文|2号探秘人编辑|2号探秘人她偷税漏税了?上一次看到她以演员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已经是2017年的事情了。在直播带货兴起后的岁月里,她踏上了这条“发财路”,开始了另一段人生。在采访中她说,自己作为童星,15岁就开始拍戏。这么多年的经历,已经掏空了她,让她无法再创作了。而在直播间内,她穿起了古装,打起了情怀牌,只为多卖出点商品。娱乐天地2023-08-12 12:10:340000韩国艺人李胜利事件愈演愈烈,波及的中国明星都有谁?
韩国男团BIGBANG不仅在韩国很受欢迎,它在中国也有很多粉丝。不过近来该男团的原成员李胜利却身陷丑闻。从夜店暴力事件到被曝疑似存在陪侍招商问题,李胜利事件可以说是愈演愈烈。或许是迫于舆论压力吧,李胜利先是宣布退团,之后又表示退出演艺圈。YG公司也宣布与李胜利解约。不过近日YG公司的股价还是下跌了不少。眼下民众都很关心胜利事件还会牵扯到多少明星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下被波及的中国明星都有谁吧!娱乐天地2023-06-04 13:49:320000

 正在请求数据,请稍候!
正在请求数据,请稍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