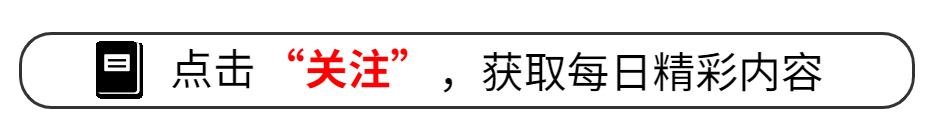在滨口龙介的电影《在车上》中,为什么要放入台湾口音?
观赏滨口龙介的新作《在车上》,台湾口音的出现无疑是一个惊喜。虽然早知道台湾新生代演员袁子芸参与本片,但并不晓得片中演员大多以本国母语演出。因此听到各国角色以各自的语言对戏,尤其是袁子芸带有台湾腔调的华语,自然是观影过程中的一大刺激。

然而,这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没有维持太久。很快地,片中的华语要素反而变成某种挥之不去的异样感,最终成为电影里最让我分心的部分。至少这是我个人的观影体验:总觉得电影里的台湾口音很令人出戏。
那么在滨口龙介的电影《在车上》中,为什么要放入台湾口音?
或许应该先说明为什么《在车上》会包含台湾在内的多国语言。本片主角家福是一名舞台剧导演兼演员,电影围绕着他制作的戏剧而展开。家福的舞台剧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由不同国家的演员以各自的语言演出,在片中甚至包括韩国手语。当然,这也意味着《在车上》这部电影注定是多声道。

实际上,家福的戏剧手法呼应了导演滨口龙介独特的表演方法论:对手的演员与其透过台词的意义沟通,不如追求语言之外更微妙的情感交流。本片之所以采用多国演员,并且在语言不通的条件下演出,正是为了追求这种弦外之音;一旦没有了方便明了的语言媒介,对手演员就不得不专注在彼此的细微情绪表现上,并从中牵引出自己更深刻的演技响应。
这对于观众也是一样道理。由于不懂得片中演员使用的外国语,再加上滨口特有的长篇对话,角色的念白很容易形成类似「语义饱和」的出神效果(就像是你长时间盯着一个字,那个字便会逐渐显得陌生而丧失意义)。于是观众的注意力便转移到演员的细微表情与动作,乃至整体情境的氛围上,效果好的时候可以达到某种难以言喻的「共鸣」──那是一种由疏离所达致的共契。这大概也是滨口作品的魅力所在。

《在车上》结尾舞台剧的韩国手语演出,可以说是这种美学的极致表现。这场戏中,两名角色面对着镜头站在舞台上,只见台上的宋尼亚从背后环抱着凡尼亚,在他面前用手语「念出」《凡尼亚舅舅》脍炙人口的结尾台词。
由于是契诃夫的经典剧目,加上之前电影里已经重复过好几遍剧本,观众不必盯着电影字幕就能理解台词;由于是手语的演出,观看演员的肢体及表情变化,跟聆听台词是同一回事;由于宋尼亚是从背后环抱着凡尼亚,在他面前挥舞着手语,两人便创造出不亚于面对面交谈的亲密性,同时却又能面对镜头与观众。

这里包含着导演的巧思:如果是在一般面对面的口语交谈中,希望对戏的演员能够正面面对镜头,那么镜头就非得插入对戏的演员之间正反打,一如滨口以往的作法。而上述手语的表演设计却可以避免摄像机的介入及镜头的切换,不致打断长镜头的情绪积累。于是,对戏的演员与观众被安置在最亲密的空间里,透过陌生的语言媒介体验到莫名的契合。
相较于上述的手语演出,《在车上》里的华语演出带给我的感受正好相反。那不是疏离的共鸣,反而更接近一种共鸣的疏离:一方面我可以直接理解这些台词的意义,另一方面却因此而产生隔阂。最表面的原因,自然是因为能够通晓袁子芸的话语,所以缩减了一些审美距离。但这并不是根本的理由,因为日本观众显然也能理解滨口电影里的日本语,却不妨碍他们观影。

在观影过程中,我忍不住开始思考其他国家的观众会有怎么样的体验。比如说,韩国或菲律宾的观众会怎么样看待片中的母语台词?而台湾的华语听在他们耳中又是怎么样的感受?或许这部片的理想观众是完全不通东亚语言的西方观众?
这并不是说袁子芸的演技不佳,或是滨口的选角不当。我相信这毋宁是台湾观众面对台湾口音的特殊反应,并且反过来揭示了滨口表演美学的历史渊源。正是观影过程中这种异样的感受,刺激我思考滨口对于台湾的再现是否有更深刻的意义。虽然下文只是不成熟的想法,但求能够抛砖引玉。
随着近几年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滨口龙介早已是台湾观众不陌生的名字,反倒是滨口对台湾的兴趣令人好奇。滨口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数度提及台湾影人,尤其是「新浪潮」的代表人物:杨德昌与侯孝贤。

在两份不同的个人十大片单中,滨口也分别选了杨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及侯的《海上花》,分给台湾片的席次并不少;其中《牯岭街》更是备受滨口推崇,滨口就曾经在访谈中提到这部片对于他的启发,尤其是在演员与台词的表现方法上。近来的新作《在车上》更是首度出现了台湾演员的身影,而这部采纳多国演员的电影也在西方各大影展备受赞誉。再度在国际影坛上听见台湾的腔调,恐怕也是自新浪潮以后的第一次。
身为一名观众,理所当然会在意这位国际名导对自身国家的关心。不过在提问「为什么是台湾」之前,也不能忘记《在车上》包含多国语言的事实。除了表演方法方面的考察,针对片中的多语策略,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挑选这几个国家?撇除韩国不论(滨口曾有日、韩合作的经验,而两国本来就关系紧密),其他国家的选择都引人深思。若是希望在片中加入华、英双语的角色,并不只有台湾这一个选项,还可以挑选中国香港或新加坡。至于为什么是挑选菲律宾,而不是其他南亚或东南亚国家,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理问题。

可以补充说明的是,关于滨口的评论往往聚焦在日常生活的主题上,但滨口的作品其实一贯具有地理空间的政治性。比如说,《亲密》在呈现青年演员的困境之外,还加入了假想的战争这个引人注目的要素;而《欢乐时光》在探索几名主角的中年危机之余,也带到311东北大地震的时代背景。把宏观的历史背景投射到微观的日常生活场景,正是滨口龙介的拿手技巧。
我们不见得要在政治的推论上走那么远,但也不该忽略片中的历史符号。不同于村上春树的小说原作,滨口将电影的舞台设定在二战原爆的地点广岛,足以见其用心。
虽然电影里没有直接着墨相关的历史记忆,但毕竟不是完全无视。电影中段,司机渡里载着主角家福来到广岛的一间垃圾焚化厂,作为两人散心的地点。渡里向家福介绍,这间焚化厂正好位于两个原爆纪念地点的中轴线上,因此建筑的设计师特意在这条轴线上保留了一条户外的走廊;沿着这条廊道可以望见大海,电影里两人就这么往海边走去,完成场景的切换。这个桥段表现出《在车上》对于空间的敏感度,提示了空间的安排如何承载着历史意义。这场戏的一颗镜头也拍出了烧毁垃圾的熊熊大火,令人联想到废墟中战火燃烧的场景。

来自北海道的渡里看着焚化厂白茫茫的垃圾从空中撒落,表示这令她想起下雪。在电影后来的转折点,渡里便载着家福前往北海道的故乡废墟(同时也是她母亲的葬身之处),在这个纪念性的地点面对过往记忆的创伤。
不同于广岛的场景设定,北海道倒是村上小说原作就有的要素;在原作中,北海道(一如村上其他作品中的雪山场景)可以说是作为一种「外部」的场所,以便从中引入神秘、超验的元素来完成剧情的转折或角色的救赎。但滨口在电影里的处理方式不同,其中北海道并不是神秘性的灵媒空间,而是作为生活劳作的场所而存在;例如,当渡里和家福与往事和解之后,两人相拥望着远方的景色,而这个远景镜头中明显可以看到背景的农家居民正在活动。在村上的小说中不可能出现这种生活感,因为这会破坏北海道作为外部风景的纯粹性。不过一如评论家柄谷行人的著名论点,北海道作为外部风景的存在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

从这个角度看,电影里频繁出现的「杀人」主题,不再是个体层次的暴力,更是战争历史的集体暴力。几名主要角色回忆过往的伤害,一再重返的道德问题是:自己杀了人,为什么不用受到审判?片中几段关键的长篇独白,实际上就是角色「认罪」的自白。但上述问题其实也适用二战的历史记忆,人们同样可以如此责问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美军,以及战后出于太平洋战略考察而免责的裕仁天皇。
如此,往返于北海道与广岛的旅途,以及东亚各国演员之间的艰难沟通,不仅是关于角色个人记忆的赎罪之旅,还涉及日本现代史的具体而微的救赎。《在车上》正是这样将历史地理的宏大格局,投射到车内狭窄空间所代表的日常场景,并透过车子的长途移动串连起微观与宏观的尺度。

话说回来,滨口龙介的《在车上》对于中国台湾的观众以及历史又有什么意义?回到本文开头的口音问题上,我认为可以在这条政治-历史的轴线上做进一步的延伸。
还是要从滨口对于台湾新浪潮的推崇,以及他独特的表演方法论上谈起。《在车上》中,作为导演的家福用一种特别的方法排演舞台剧,可以看做是滨口的夫子自道:在排演初期,演员只是一味地反复诵读剧本,而且被要求不带感情地念台词。电影里袁子芸扮演的珍妮丝曾经对此表达不满,用英语抗议道「我们不是机器人」。但电影稍后珍妮丝也理解了导演的用意,指出透过反复读本而彻底记忆台词,在演出对手戏时反而可以忘却台词的意义。
这种技巧帮助演员专注在对方的细微情绪表现上,从中引导出双方更深层的演技。不妨暂且将这种方法称作「语言的疏离」。滨口在本片之前就已经开始运用这种方法,不过《在车上》的剧本更加入了多国语言,使得「语言的疏离」在语言不通的极端情况下变得更加显著。

这样的手法其实不完全是滨口的独创,可以从历代的电影大师中看到踪迹,比如布列松及卡萨维蒂的方法论。关于滨口如何继承西方大师,许多评论已经谈得相当深入,倒是本地导演杨德昌对于滨口的影响,不知为何比较少论及。善于发掘演员潜质的滨口,照理说应该是站在规训演员至极的杨德昌的对立面,但滨口却自承杨德昌带给他的启发。他在访谈里是这么说的:
「我是从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发现到这种处理方法。演员本身未必清楚这些对白背后的含意,但演员又可以表现得好像很自然,发自内心地念着这些对白。我务求要制造出这种状态,令这些对白显得很有张力。」

滨口能够从《牯岭街》发现这种手法,自然跟杨德昌及新浪潮的美学脱不了关系。虽然不清楚滨口到底是从《牯岭街》的哪一段得到如此灵感,但我猜测片中「少年」的演技想必令他印象深刻。出于剧情的需要,《牯岭街》必须采用许多十来岁的少年演员,而这些少年自然不会有成年演员的成熟演技。与此同时,台湾新浪潮力图摆脱以往片场的造作姿态,专注于捕捉生活的「真实」,因此并不吝于启用素人演员(滨口早期的路线也与此接近)。《牯岭街》的男女主角小四、小明正是第一次登台演出的素人,饰演小明的杨静怡日后甚至没有踏上演员的道路,只在本片短暂的夏天里昙花一现。
不过杨德昌究竟不同于侯孝贤,后者往往融入这些素人演员的生活,捕捉他们最自然的日常对话甚至脱稿演出;相反地,杨德昌是著名的控制狂,务必要演员一字一句服从指示。而这些生涩的年轻演员显然不可能完全掌握《牯岭街》复杂的剧本,在某种程度上只能是熟练地背诵台词而已──我想这正是为什么滨口会从中发现「语言的疏离」。

但滨口未必意识到──事实上,这样的立论或许也还不够充分──「语言的疏离」不只是新浪潮的独特手法,更可能是台湾现代史的产物。
当初滨口从《牯岭街》感受到的「语言的疏离」,或许不只是年纪的问题,更在于台湾新一代演员并不知道如何在镜头前表演「普通话」。象征地说,台湾的华语表演仍然处在语言学习的少年阶段。既然杨德昌不像侯孝贤那样朝乡土母语挖掘,或是像蔡明亮那样往沉默的境界迈进,便不能不走向有如机械一般疏离的语言表现;虽说这正好也适合杨德昌对于台北都市生活的呈现。

有意思的是,与杨德昌的《牯岭街》相呼应,滨口在个人十大片单中所选的另一部台湾片《海上花》,恰巧是侯孝贤最脱离演员母语的一部片。《海上花》的演员为了饰演十九世纪的上海欢场,特地去学习当地方言吴语。而《海上花》改编自十九世纪末的吴语小说,书中舍弃通用的官话而采用地方的吴语,实际上也跟现代中国的普通话问题相关。不晓得滨口是否从中感受到跟《牯岭街》相似的「语言的疏离」?

谈到这里可能已经「出戏」太深,偏离了《在车上》这部片的讨论。但《在车上》里台湾演员令人出戏的口音,正是本文思考的起点。从这点出发,本文一方面尝试在《在车上》发现日本现代史的线索,另一方面又从滨口的电影手法上溯自战后历史的渊源。
至此我们的讨论绕了一个圈,不妨就在这个历史的闭环之下收尾:台湾的口音作为《在车上》多国语音声道的一环,在电影里参与了现代日本的历史记忆命题;而历史上日本战败所牵动的东亚格局导致了台湾电影的语言问题,其中新浪潮的语言处理启发了滨口龙介,进一步促成今日这部多语系的杰作。身为台湾观众,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待《在车上》的历史意义。
她曾是选美冠军,却热衷于演打戏,如今演《半生缘》会火吗?
作为亚姐冠军出身的董玥,不仅有着出众的外貌,更是在各种谍战大剧中却展现了英姿飒爽的一面。正是因为这种反差感,让观众对董玥产生了深刻的印象。2006年,董玥参加了香港亚洲电视主办的亚洲小姐选美比赛。凭借着出众的外貌,董玥顺利在亚洲小姐中国区的评选中荣获了总冠军。正是因为这次比赛为董玥累计不错的人气,董玥也因此收到山东电视台《综艺满天星》的邀请,成为该节目的主持人和颁奖嘉宾。娱乐天地2023-06-01 07:21:010000性暴力,暗交易,剧组宿舍当后宫,这韩国纪录片看的我头皮发麻
韩国有个R片导演金基德。他的电影里面充斥着“性”,充斥着逼良为娼的占有,隔着玻璃的窥淫欲,反复发作的斯德尔摩综合症,挑衅与变态的犯罪,在他的电影随处可见。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导演。几次登顶欧洲电影节的最高殿堂,他拿了三次大奖。第一次是他的《空房间》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拿了最佳导演奖,第二次《《撒玛利亚女孩》在柏林电影节拿了最佳导演。第三次就很有历史意义了。娱乐天地2023-04-23 14:03:530000五部都市悬疑待播剧,一部比一部有爆款相,哪一部值得熬夜追?
近日,都市悬疑剧《不期而至》正在热播,腹黑律师与单纯小白兔的设定,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再加上蔡文静、彭冠英的默契配合和完美演绎,让人设更加吸睛。随着这部都市悬疑剧的爆火,让大众对于这一题材的作品更加期待,除了《不期而至》之外,还有五部待播都市悬疑剧,一部比一部有爆款相,一起来看看哪部值得熬夜追吧!第一部:《刑侦笔记》娱乐天地2023-05-27 13:03:220000网红牛魔王夫妇分手,养牛亏损600万不敢结婚,女方回应真实原因
文|顾远山编辑|顾远山“从成都到东北,从24岁到27岁,这一路她陪你吃过多少苦?遭了多少难?可到头来却只换来一句疏远到极致的‘恐婚’,我都替她感到不值!”他是坐拥近千头牛的养殖大户,也是网友心中抱得美人归的成功人士,彼时的他,不知被多少网友发自内心地羡慕。娱乐天地2023-11-29 12:22:560000二手玫瑰夺冠,惹起争议,网友:节目失败
注意看,二手玫瑰居然获得了乐夏的总冠军,而瓦依那遗憾错过冠军。近期,《乐队的夏天3》总决赛终于如期来临了。二手玫瑰更是凭借一首《仙儿》勇夺冠军,这首《仙儿》融合多种新元素,也融入了吉他,民乐,贝斯,鼓,笛子,琵琶等多种乐器,让观众听得如痴如醉,并且二手玫瑰的舞台风格别具一格,舞台感染力也非常棒,可以说这个冠军算是实至名归。娱乐天地2023-10-25 18:38:05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