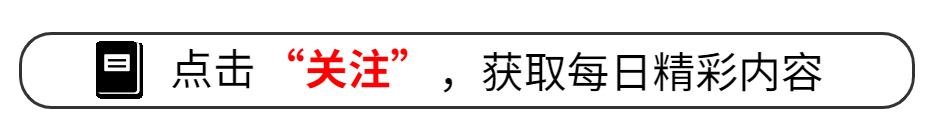诺兰影片中构架的破裂迷失、虚实参半空间,增添叙事的荒诞与深意

列斐伏尔理论框架之下的“社会空间”,主要由人们的社会行为交织构成,人类的施动范围和结果,决定了社会空间最终的状貌。
将着重关注社会空间这一综合概念体里的权力关系属性,走入对抽象性身份问题的探讨。作为“空间三元辩证法”里真实生活的空间,生活主体在社会空间里的行为规范和文化标志,总会经历空间表征的制约与影响。

这种社会意义便依赖着一系列社会性活动去发掘,列斐伏尔的理论放大了人类行动对社会空间的能动作用,这也意味着电影里着重分析角色人物行径,也可反推出“受制于人”的社会形态背后的价值观与意识语法。
诺兰在叙事空间里的社会性展示立足于人物间的社会关系纠葛之上,以及社会成员在组成的团体,如家庭、组织里的角色身份中。

他的叙事处理让人物的社会关系与成员间的组织团体总是陷于破裂崩坏的状态,此类社会空间形式,也复杂化了剧中角色或群体遭遇的困难或危机,矛盾的尖锐刺激也成为了推进叙事深入发展的强劲动力。
“一心渴望哪怕能遥见从故乡升起的飘渺炊烟” ,自荷马史诗吟唱起的奥修斯,“归乡寻家”便成为了西方叙事传统里的惯用行动诱因,是电影艺术里人物常见的行为动机。

作为社会空间里最为亲密的场所,家庭组织抑或更为大范围的居住家园,诺兰在其中构建了太多爱情与亲情的冲突,填满了欲望与责任的较量。
知名学者戴锦华也表示,自电影《绿野仙踪》问世之后,对“家”的殷切期盼便成为了美国大众文艺主题里最为常见的表达,成为一类基本动力结构。诺兰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社会空间里的情感线索,构建起如叙事支撑般的存在。

除却叙事内容元素的惯性设置之外,“家”单位作为日常生活里生产关系最为细化的集合。成员间身份关系的断裂,或者生命个体的行为改造,都会让整体社会空间的秩序发生畸变,从而让空间指代的象征性情感也随之抽象。
如诺兰的处理下,主角往往陷于家园破裂、家庭残缺的悲象之上,以家人的亡故诱发起后续事件,而丧失亲人的悲痛之源,皆为后续仇恨意识的发端。

例如《记忆碎片》里谢尔比的出场,便是在替惨死的妻子追凶的道路之上;《致命魔术》里导致安吉尔与波登反目成仇的关键事件也是安吉尔妻子的意外之死;
《盗梦空间》里亡妻的形象一直是柯布心中梦魇般的存在,为其行动增添着无尽的潜在威胁……爱情与婚姻,在破裂缺失的前提下,一反往日女性角色所带来的慰藉作用,更甚成为了一种悲剧性的起源。

与惯性思维里主角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最终与家人合美欢聚的圆满落幕不同,诺兰消解了寻回之旅上的温馨与美景,展示出的全然是家庭成员逝去后,亲人间社会关系的分崩离析。
除却家庭成员身份的缺失,造成家庭这一最基本社会群体单位的不完整性外,诺兰还以小见大,通过一种“家庭”的消逝,传递出对失落家园的追寻。

“蝙蝠侠三部曲”里布鲁斯·韦恩因为意外年幼失去至亲,这场城市罪恶里映射出的是哥谭市这一赖以生存的家园已然被黑暗势力摧毁。
斯人已逝,家难成家,韦恩决心重振哥谭市正义的做法其实是为了寻回理想家园;《星际穿越》里的情形同样类似,地球生态的破坏,迫使库珀一行人与家人分离,寻找新的宜居环境。漫长的太空穿梭,已让库珀与亲人形成了巨大的时间差,最终重逢时,儿子早已离去,90 岁的女儿也在弥留之际。

当库珀重返全新的生存空间,身边再无亲人常伴时,他是否真实寻回了心中的家园,仍然存疑;而在《敦刻尔克》中,诺兰也未曾被宏大的战争时局遮蔽双眼,选择从战士们一心求生、渴望归家的心理入手,创造了一场生存迷局。
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诺兰电影里的角色对于家园和家庭这一社会关系产物充满执念,导演对于社会空间预设的不圆满性,让他们一生都在“寻家”道路上。

“家”图腾的失真,标志着诺兰认知里的日常生活氛围将会迎来异化分裂。因为列斐伏尔曾预言,资本主义生产力日益壮大的结果,便是将工业社会的抽象性特征植入进现实生活的感性刻画里,从而遮蔽原有的真实性。
宛如一个符号世界取代了真实场域,糅合幻觉掩饰社会的每一处角落。社会空间成为社会关系与秩序的映射,其象征意义自然随之更替。诺兰便直接将此类空间形态设置在了原有的对立面上,展示影片人物是如何新设社会关系又同时被其制约,陷落困境泥淖。

家与家园不约而同地成为了角色心中生存意义的象征,为了弥补已有的遗憾,他们不能停下寻找的脚步,哪怕“失家”的事实难以回逆。
在这一社会关系的理解上,可以看出诺兰对传统形式结构的反叛,虽是以家庭、家园的愿景作为人物行为动机,但却在结局从不设立失而复得的喜悦,取而代之的是失去即逝去的永恒毁灭。这样的叙事表达,不禁让诺兰的电影拥有了个人特色的哲学色彩。

处于社会关系里的人物并非孤岛一般的独立存在,落入人情网络里的主人公在交往处事时扮演何种角色,也是值得审视的问题。
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实践让填充其间的社会关系拥有了一类精神文化意识,以人物的活动语言、思维、意识与社交反渗着社会空间形态。故穿透社会空间表层意义,发掘其核心的社会价值观念与社会矛盾危机才是关键。

因此,诺兰总是以一股强大的排斥力将自己作品里的角色推至“边缘地界”,借一种坚持不懈的抵抗和坚守使命的孤独感,空间生产运营模式对个体精神意识的消解。
人物在环境胁迫下的身份危机和自我怀疑,暗喻出社会空间里的价值观念交锋和层层矛盾冲突,将其作为导火索点燃后续的戏剧张力。特征之一便是诺兰电影里人物的身份标签多样化,且其中最为接近核心矛盾的身份,被遮蔽得最为严密,往往作为隐晦线索深埋于叙事发展中。

“蝙蝠侠三部曲”里的布鲁斯·韦恩,集罪犯、影武者联盟门徒、韦恩集团总裁等多重标签于一身,但真正推动故事深入的,是其韦恩财团继承人和蝙蝠侠身份,表面上他以花花公子的形象纸醉金迷于各类社交场合,暗线里他以蝙蝠侠的伪装惩恶扬善,匡扶哥谭市正义。
前者仅为表象,后者才是韦恩完美品质的展示,类似的身份设置还发生在《盗梦空间》里的道姆·柯布、《星际穿越》里的库珀等人物之上。

诺兰以隐秘的基调,为人物社会身份的建立增添神秘性,且让其通过家庭、聚会、亲人、朋友等社会活动与关系树立,并让观众辨析得到各个身份间的重要程度差异,最终挑选出根连叙事核心事件的形象标签——即韦恩的“蝙蝠侠”身份是通过蝙蝠战衣、战车座驾、秘密基地以及一件件惩恶扬善的事件建立起来的。
诺兰以身份驱动让角色有所作为,又令其身份在实践进行中得到巩固。特征之二在于诺兰电影里塑造的人物众多的社会身份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往往最难以被承认接受。

以《星际穿越》为例,主角库珀在地球末日里以农民身份自居,但他同样是NASA前优秀宇航员,但这一身份在此时是不被需要的。面对地球当下的饥荒现状,墨菲的老师说,库珀的航天工程师身份远不如一位可以让人饱腹的农民意义深远。在现实的生存威胁下,世界需要好的农民。
同时,这种身份危机在布兰德教授的话中也有所印证,但恰恰正是库珀等人这种“不合法性”的身份,最终引领人类寻得了新的栖居所。

同理,这种社会身份的排斥,还表现在“蝙蝠侠三部曲”中布鲁斯·韦恩背负污名后,所遭受的抵制与反对声音中。这种身份迷失的处理,会让身份主体陷入心理怀疑和自我否定之中,最终演化为一类客体世界里的社会性认知缺失。
因为自我知觉限界模糊的缘故,逐步积攒的焦虑也会动摇自我认同知觉的稳固性。这种社会身份迷失错位,为诺兰构建起电影人物的行为逻辑,影片中的角色因此笼罩在一类矛盾的悖论之中:虽然社会身份在片中不被周遭人认可,却收获了观众的同情与共鸣,让诺兰电影的感染力持续生长。

诺兰也正是巧用错综复杂的多重社会身份的掩护,让影像里的一切行为事件变得“顺理成章”起来。更为重要的是,人物的社会身份内涵在资本的进步的景况下竟能如此轻易被瓦解,也暗含了一份导演对于社会空间生产高速运行,是否也会偏离人类真实需求的忧思。
这种生产关系下的永恒矛盾,带来了自由解放,但掌控与压制又会同步。恰如斯图尔特·霍尔所言:“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做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

作为反映人物内心活动的精神空间,诺兰以梦境和记忆游戏,拼贴起片中人物的心理刻画。
精神空间在列斐伏尔的表述中具有构想性,是超出感官感知的抽象空间。作为精神化、理念化的符号,该特殊空间充满了欲望与控制,象征性内容的潜藏,让诺兰如何诠释这仿真又有别于真实的世界,成为焦点。
诺兰在借用梦境与记忆机制完成叙事需求时,主要使用以下策略:

一是将精神空间的场景全然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直接以人类梦境或思维运作的机制深度挖掘,使之成为推动剧情演进的线索;二是以精神空间的组成内容,创新故事题材与内容,新颖的叙事设定,成为了良好观影兴致的发端;
三是以精神空间的运营方式深入化解叙事框架,如在《盗梦空间》里,诺兰就赋予了梦境世界完整世界观,有如公式般的运行规则;四是以精神空间的虚实之辩,增添着叙事的哲学意味。弗洛伊德本我、自我和超我概念,成为了诺兰在剧中深层次挖掘角色内心及潜意识的思路,据此一步步抵达人物欲望的本质。

而思念与想象组成的记忆部分,在推动情节行进中发挥着十足的迷惑作用。梦境的飘渺虚无,却又与人的真实意识相勾连,角色所经历的记忆与情感,却又会因人的本能而刻意加工,变得不真实。
由此而来,精神世界充满了虚实相间的气质,而梦境与记忆,在其中被渲染得既困顿压抑又充满欺骗性。这种亦真亦幻的效应,引发着观众的反复思考,隐约牵动着观众的求知焦虑。

在弗洛伊德关于梦境的内容研究中,认为人之所梦与其被压抑的无意识幻想具有联系,因而梦境被作为人潜意识的反射。
借由刻画梦境空间的形态来讲述角色的内心故事,这给予了诺兰创作《盗梦空间》的基础。电影里的主角柯布是一名植梦师,他与团队成员通过建立梦境,掌控目标对象意识,来侵入概念,使概念如潜意识般印刻于脑海之中,最终左右目标的行为方式。

而闯入意识空间之所以能够成功,利用的正是人物痛苦过往演化而来的伤痕梦境,这种缺失的郁结在人物的潜意识里占有重要比重,一旦满足,便得以操纵和支配人的思想与行为,如柯布等人入侵费舍得梦境时,植入的正是他父亲出于对他的保护,没有让其继承公司的概念。
费舍潜意识里本就渴望父亲的关怀,对父爱充满期待。原本悲剧性的梦境氛围得到逆转,在潜意识里的渴求得到满足后,柯布团队的任务成功。顺着弗洛伊德的思路,诺兰将个体心理的基本组成和能量来源归类于人的潜意识领域。

这一具有自我愿望冲动、表现方式、运作机制的精神领域,从人物的事实经历和精神需求里汲取题材,以梦的情感伴随人物的成长始终。
“蝙蝠侠三部曲”里的韦恩幼年目睹了父母被杀害的惨状,这种恐惧常年以梦魇的形式阻碍着他;当其童年掉入枯井受到蝙蝠惊吓时,也是父亲伸出援手,将他拯救。这些场景在韦恩的梦境空间里反复闪现,充满了伤痕气息。

一方面他想念与尊敬父亲的勇敢,同时又因当年胆怯造成父母离世而自责不已。同理,影片《致命魔术》里安吉尔梦境中反复出现妻子溺亡的场景;《白夜追凶》中多莫总是梦回开枪误杀同伴的瞬间。
在诺兰的塑造里,梦境的甜美感被完全消弭,悲剧性十足的色彩代表着对人物的生活的深切阻碍与羁绊。因此,对伤痕梦境的跨越,也成了诺兰影片里人物心灵成长的必经之路。

在诺兰的电影表述里,记忆的出现总是伴随着浓厚的欺骗色彩,且常以“自欺”的方式呈现,角色既是说谎者,又同时为被骗对象。诺兰在访谈里将这类情况归纳为:“你在和你自己下棋,却没有意识到你是你自己的对手。”
自欺欺人记忆的诞生源自本能里自我保护的意识,根本上是难以承受事实真相所带来的创伤疼痛。这类致命的精神创伤在诺兰作品以爱情叙事最为典型,《记忆碎片》里反复交叉的幸福记忆与凶案现场的片段,代表了谢尔比在直面与逃避间游移不定。

相似的爱情祭悼还发生在《致命魔术》里安吉尔对亡妻的眷念,《盗梦空间》里柯布对妻子自杀的介怀中。诺兰多部作品里女性角色的缺席,让男主角不禁患上了罗兰·巴特的“恋人之死”症状,痛失所爱的精神挣扎,让人物陷入了记忆迷雾当中。
此处以《记忆碎片》做详尽分析。谢尔比罹患的“短期记忆丧失症”,让记忆成为了一种扭曲变形、重构再现的产物。在他眼中的记录工具——记忆,全然不再是事实的反映,而是演绎的结果。

记忆的真实性色彩在影片中被完全抹去,断续的印象闪回,宛如紊乱的干扰,让脆弱的模糊轮廓抽象失真。记忆召回与定位的精准性功用也荡然无存,转化为了一种纯粹心理刺激的回应,经由诱发,还原一类“被重构”过的影像。
“短期记忆丧失症”让谢尔比的记忆拥有了被“名正言顺”干扰,他仅记得妻子遇害遭遇暴行的印记,选择性遗忘了自己误杀妻子的事实。这也导致他每次在即将触碰真相时,总会丢失关键性线索,从而只能继续“虚拟”出下一位复仇目标,继续追凶。

无论是警察泰迪,还是假想出的萨米·杰肯斯……这些角色都是谢尔比移情内心创伤、拒绝直面后的幻象。
正如泰迪在影片中所言:“为了替自己制造一个解不开的迷……到处扮演侦探,一直活在梦中,有死去的妻子可供怀念,有生活的目的”。

看似清晰无比的记忆线索,实则走向的是惘然荒诞的命运悲剧。诺兰剧中的人物,总是乐于虚构自己理想的生存境遇将自己困囿其中, 这些角色几乎都在知觉上暗示自我记忆环境的真实性,甘愿被“自欺”记忆束缚。诺兰借这样的精神空间形态,增添着电影叙事的荒诞感与深意。
盘点2022年不幸去世的13位香港明星,谁最让人惋惜?
曾几何时,香港娱乐圈被称为“东方好莱坞”,是多少演员的追梦之地,然而近几年一个个熟悉的面孔离去、不少港星齐齐转战内陆,港圈也逐渐没落了。一眨眼,2022年就要过去了,香港娱乐圈已经有13位资深戏骨去世......眼看着这些代表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熟面孔一个个离去,港圈的辉煌即将落幕,令人感慨万分。1、卢雄74岁娱乐天地2023-05-14 14:37:420000一恋美女主播,二恋小10岁女星,如今56岁再婚娶同居10年女友?
有些香港男星挺会保养的,他们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陶大宇就是如此。陶大宇已经56岁了,但他并没有发福,他的身材保持得很好。近日,陶大宇被曝疑似再婚了。有报道称他再婚娶同居10年的女友为妻。娱乐天地2023-06-08 23:05:170000她是新加坡最美女星,演《笑傲江湖》走红,如今只能拍烂剧?
说起范文芳,在新加坡可是人尽皆知。范文芳是新加坡的名片,被称为新加坡最美女星。范文芳属于气质温婉的女明星,非常耐看。她的长相宜古宜今。80后很多人都看过她演的电视剧。娱乐天地2023-05-29 02:55:290000一代女神,仙逝28年
“青霞!丽君!”“你在乱叫什么?”“我想看下林青霞、邓丽君她们在不在,你没看报纸吗?她们最喜欢到康城来,脱光了衣服游泳,我想找她们签个名嘛!”“她们把衣服都脱光了,哪还有笔呀!”“我有啊!”这一幕,发生在1990年的法国戛纳海边。那一天,吴宇森带着周润发、张国荣和钟楚红过来拍《纵横四海》。看到当地的蓝天、大海与沙滩,周润发和张国荣突发奇想,给电影加入了这个经典桥段。娱乐天地2023-05-26 00:45:230000央视女主持海霞嫁大11岁教授,离开《新闻联播》后,事业出现转机
“祝贺央视主持人海霞和清华教授罗永章新婚快乐!祝你们百年好合!”随着婚礼主持人婚礼贺词,一对年龄相差整整11岁的新婚夫妻,在朋友亲人的祝福声中进入了婚姻的殿堂。女方是主持央视《新闻联播》《晚间新闻》《早间新闻》的著名主持人海霞,而男方的名字是罗永章。罗永章有何身?年龄与海霞相差11岁的他又为何能得到才女的芳心?海霞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央视的大腕主持人呢?娱乐天地2023-08-13 14:07:07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