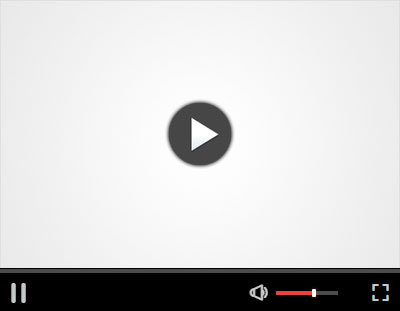在战争之后,日本电影中,如何表现价值观的迷失

市川昆最广为人知的电影还是以改编剧本为代表的,诸如《炎上》、《心》、《破戒》等作品,或者是他以“刻画日式传统之美”的女性题材之作,如《日本桥》《细雪》《少爷》等,但令人意外的是,市川本人早期其实非常热衷于拍摄揭露病态社会的讽刺喜剧。
上个世纪50年代是市川昆电影生涯的黄金年代,50年代的前期,他的“讽刺喜剧三部曲”:《亿万富翁》、《满员电车》、《浦桑》受到观众喜爱,后期他继续从讽刺性视点出发,拍出了“太阳族”电影《处刑的房间》。

和木下惠介一样,他在电影创作过程中经历了从喜剧到悲剧的转变,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在寻找人道主义,但并没有找到。
这类电影描绘了战后金钱至上的社会,讲述了年轻人面对未来的困惑以及各种小人物的艰难处境,在面对这样的人性相关的议题时,市川的笔触显得尤为成熟,这一系列作品使他获得了“战后小人物挫败心声代言人”的声誉。

人口增长失控的后果在战后逐渐显现,食物匮乏、住房紧张加之企业倒闭失业严重,严峻的社会现实让普通人苦不堪言。与此同时,美苏争霸背景下,原子弹、氢弹带来的恐惧依旧存在。
《亿万富翁》刻画了腐败的政客逃税时的丑恶嘴脸,与之相对的,是有18个孩子的贫困家庭的艰辛生活,其中一个女孩在原子弹爆炸中失去了家人,为了报仇,她白天上班晚上在阁楼里制作原子弹,荒诞且讽刺。

市川的母亲与姐姐皆因原子弹逝世,他在面对此类问题上时显得尤为痛苦。与黑泽明的《活人的记录》中的展现的战争后遗症有类似之处,以闭环结构残酷地再现了战后日本社会看似一片平静的表像下,因战败而造成的经济萧条与生活贫困问题更趋尖锐化。
《浦桑》改编自漫画家横山泰三的连载四格漫画,刻画了战后8年日本社会,有不少的战争遗风。即使没有交代野吕老师的身份,但从他每次看到游行的警察预备队和吉普车都捂住眼睛,可以看出是经历过战争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

野吕为了再就业不得不进入与军火相关的企业,虽然怀着对战争根深蒂固的怨恨,但他依然有需要背负的责任,只能适应着时代生活下去。最后一幕的野吕在清晨的街道上徘徊,慢慢走向画面深处,他孤寂的背影让人联想到《现代时报》的卓别林。
电影以被昭和二十年代经济下行压力所困扰的野吕为中心,展现了共产党示威、战犯回归公职、就业困难等具有时代感的画面。

野吕在车祸中右手受伤,示威中则左手受伤,表现了他思想上从右到左摇摆。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对人的压迫,普通人在面对战争时感到无可奈何,但并无力量撼动这棵大树,野吕对参与战争感到愧疚,与狂热的同事们格格不入。
他的女儿在银行里数着山一样的钞票,漫画似的方式讽刺了国家和银行有大量的资金但老百姓们依然过着贫困的生活,与野吕被学校开除相对的是腐败的政治家们哪怕进了监狱都可以赚钱。

时代的一粒沙,落到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战后普通人生活的艰难困境被市川一一展现在电影里。市川的讽刺电影受到了日本国内影视圈的大力推崇,他一跃成为日本影坛最炙手可热的导演。
1956年,市川昆41岁,经历了“二战”,感受过战后颓丧的氛围以及“忍”字当头的空虚生活,他对于普遍存在于日本民众心里的焦虑不安以及年轻人焦灼躁动都有了更深的体会,《处刑的房间》在此时横空出世,相较于《疯狂的果实》中残余的青春气息与《太阳的季节》中盲目的反抗,本片展现的集体焦虑的极端性外化与对其成因的深度探索使得这部“太阳族”电影达到了其他电影所未及的高度,表现出一种更为复杂的“反抗意识”。

上个世纪50年代,无数以青少年为主的电影在世界各地上演,风起云涌的“新浪潮”时代席卷全球。
电影中必然会出现的各种意象包括:烟酒、暴力、性爱、逃学、歌舞以及由对时代变迁的不同理解导致的与父母之间紧张的关系。《处刑的房间》同样展现了年轻人恣意张扬的个人主义至上的生活。

主人公岛田胜三是早稻田大学的一名学生,他总是对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颐指气使。胜三与同学为了筹办一场舞会而向父亲行骗,全然不顾对方赚钱的辛劳,在舞会上他认识了显子并将其伤害,醒来后的显子爱上了他,却依然被他抛弃。
最后这个叛逆的少年去找朋友讨债,反被一群不良少年围攻,这群人企图杀害他但又不敢独自下手,最后他被显子持刀刺伤,浑身是血不服输似的爬出小店。

市川在这部电影中刻画了一个反叛、自私的年轻人,胜三所处的时代是导致他情感异化的重要原因,导演也将时代的特征通过父与子沟通的困境予以呈现。
观众透过摄像机得以窥见在物质并不匮乏的年代,年轻人毫无目标地生活着。电影开始时沸沸扬扬的学生运动与父亲在田间孤独行走的画面交替出现,年轻人把对未来的迷茫投入火热的学生运动中,可生活的压力并不会就此消散。

胜三完全不为将来做打算,只顾求感官刺激,需要朋友和舞会,认为伤害女人是“天才才能想出的办法”,就这样一步步跌入了深渊。
电影中有一场橄榄球赛,少年们在球场上奔跑和厮打,毫无青春活力而言,只剩满屏的愤恨。胜三在电影中有多次奔跑的画面,如一只野兽,有无尽的欲望需要宣泄,需要通过漫无目的的斗争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他办舞会、颠覆父母的想象、强奸女性都是为了强调自己的价值。

追求刺激、企图通过暴力行为达到目的的少年们,一步步走向了未知的深渊。这种反叛的表现,与影片中多次出现的学生运动的画面结合在一起,展现了战后日本社会“太阳族”青年们的生存现状。
然而,在学校里努力上进的青年也并非就有所谓的光明的未来。日本的教育逐渐沦为输送职员的统一化工厂,各种社会病也随之出现。

《满员电车》中的民雄毕业于日本顶尖大学,工作后每天起早贪黑,和一群像丧尸一样的公司职员前往车站。
到达车站后,他们被装在叫做“电车”的箱子里,向公司“发货”。职员们每天都因为公司的“合理”制度而被迫做不合理的工作。

比起选择优秀的员工,老板更偏爱低调的人,默不作声被认为是一种美德,高学历反而会妨碍出人头地。既不要求工作效率高,也不要求削减不必要的预算。既不需要意见,也不需要个性。
在传送带上流动的贴着同样标签的啤酒瓶是年轻人的象征。社会对心理咨询的需求会越来越大,这些其实都是社会异化的警报。

职员们一辈子为了房子车子等物品奋斗直到死亡,彻底沦为商品拜物教的奴隶。年轻人听从父辈的教诲,从最高学府毕业,高举独立的旗帜,意气风发地走向社会,但现实却与理想完全不同。
很多人患上了心理疾病,其中还有人自杀。如果说“太阳族”电影以反抗姿态完美展现了青年观众们对现实的不满,那么《满员电车》则给了其他循规蹈矩的青年人致命一击,市川昆有意将成年世界的伪善展现出来,对日本社会的种种规矩条理以及约束进行批判。

这几部作品都充满对社会正义的严肃关注,但值得一提的是,市川早期的讽刺电影还带着些法国新浪潮色彩。
《穴》描绘了一出女记者企图揭露警察贪污案件却反被解雇并惨遭财阀暗算的复杂戏码,与特吕弗遗作《情杀案中案》有异曲同工之妙,絮絮叨叨的女主角牵扯出的一出闹剧,企图揭露社会不为人知的可怕一面却因势单力薄成为众矢之的。

希区柯克式悬疑电影的风格故事碰撞上弗兰克·卡普拉的叙事格调——登场人物滔滔不绝地说出具有时代特点的论调,悬疑中带着一丝幽默,讽刺中带着一股心酸,又以几处非线性的叙事增加电影的神秘感,别出机杼,小成本的讽刺电影质感甚至好于名篇大作的改编剧,在这一点上,编剧和田夏十功不可没。
对于市川而言,喜剧和悲剧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导演自由穿梭于其间,游刃有余地处理着这些角色,对于观众而言,这些电影是窥探战后日本现实的一扇窗。

《浦桑》里的中年教师被学生邀请参加共产党示威,因此被学校开除不得不进入最厌恶的军火行业;《亿万富翁》聚焦于一个无人相助的新入职的税务所职员,穷人无钱可交,富人巧妙逃税,这位懦弱的职员于是陷入困境;《处刑的房间》中的少年犯下强奸罪却不以为然,可即使像《满员电车》里的大学生一样勤勉努力,却也只是成为一个没有个性的齿轮。
从记者到老师、年轻职员以及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这几位主人公虽然可以看作是稳定的雇佣劳动者,但随时面临着被解雇的风险,而造成这一风险的便是战后政府对于恢复经济提出的各种要求。

还包括贫困的多子家庭与沉溺战争的年轻女性,以不同的角度展示当时人们的心理状态,日本诚然不乏恋战者,但依然存在野吕这样的反战者,而这样的人群是需要打开一扇窗户被看见的。
市川在拍摄这些电影时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在“二战”后日本文艺作品普遍偏重理论性与思想性的大社会环境下,市川冷静地思考,他对于战争的反思不仅体现在两部战争作品中,更反映在早期的这几部讽刺喜剧中。

正如小林正树所说:“在观察过人性的历史之后,人很容易变得悲观,你不得不努力变得乐观起来。”
他与市川对日本社会的细微观察,不得不以此类讽刺风格呈现。这样的悲剧性只能以市川对戏剧性的情节、节奏的敏感性以及不断增强的听觉、视觉美学来调和。
1977年捷克文艺电影《玫瑰色的梦》
娱乐天地2023-05-10 12:31:090000坑了朱丹1600万的人已经被揪出来了!大家还发现周一围也藏的很深
原来我们一直都被周一围和朱丹这两口子给蒙蔽了早先朱丹在节目中对周一围的百依百顺都让网友们非常吃惊更是让李诞和傅首尔觉得她就是恋爱脑。没想到今天被各种视频误导的朋友都被集体打脸原来周一围才是顶级的恋爱脑,他一直藏着掖着。在节目中朱丹自曝被曾经最好的闺蜜利用她们之间的信任通过非常简单的手法就骗走了她1600万。尽管朱丹反应过来后马上报案,但也于事无补娱乐天地2023-12-01 13:30:240000盘点娱乐圈八大男星的高颜值小姨子,看看谁最美?
娱乐圈有不少男明星娶了一个很漂亮的老婆,但是没想到连小姨子的颜值也很高哦。作为80后的子女,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但是也有一些是例外的,家里有个漂亮的小姨子,男明星们与她们的关系将更为神秘!下面,就为大家盘点娱乐圈中男明星们八位高颜值的小姨子吧,看看谁最美!1、鲍莉娱乐天地2023-05-28 22:40:530001她曾是选美冠军,嫁入豪门后老公欠债12亿,如今复出为老公还债!
现在结婚一般都讲究门当户对,对于娱乐圈的女明星们来说,嫁入豪门是一个不错的归宿。是不是真爱暂且不说,各取所需的情况还是存在的。但是嫁入豪门不代表就万事大吉了,毕竟豪门也有破产的时候,徐若瑄就碰上了这样的问题。娱乐天地2023-05-27 15:00:590000她与吴宗宪绯闻不断,愚人节公布结婚消息,如今41岁悄悄离婚?
我们会发现,在娱乐圈其实有很多的演员明星等他们本身都不是专业演员科班出身。但因为自身条件不错而被发掘而出道。林立雯就是如此,她本身是毕业于国立台湾海洋大学航运管理学系,但因为拍摄了一个MV而被发现。最终成为了一个演员,同时也是一个主持人影视剧代表作品有《MVP情人》、《香草恋人馆》等。娱乐天地2023-06-07 19:55:22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