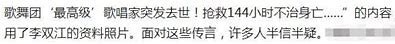第六代导演镜头下,强烈的语言符号,是一种文化象征也是精神体现

布尔迪厄的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可以分为合法语言与非合法语言。合法语言是指官方语言,它是受政治支配的产物,被主流文化所认可,一切的语言实践都要以合法语言作为尺度来衡量。而非合法语言处于被支配地位,是不被官方合法语言所认同的。
与主流话语相比,脏话显然是一种非主流的非合法语言,它以风格化的戏谑、调侃、自嘲、谩骂等形式表达着对合法语言的对抗。
霍尔在《通过仪式抵抗》一书中认为大部分亚文化都表现出了自己与他者的世界在语言上的隔阂,因此脏话作为一种与合法语言在语言上有着巨大隔阂的非合法语言,是一种典型的亚文化。

它彰显着亚文化对主流文化和文化霸权的抵抗与反叛,“脏话”这种亚文化也成为第六代导演影像中的重要亚文化语言符号。
在张元的《北京杂种》中,去他妈的、我他妈、真他妈丢人、瞧你那怂样这些脏话频频从那群游荡在北京边缘的摇滚青年和小混混的口中蹦出来,在乏味与孤独的日常生活中,脏话已经成为那群“北京杂种”的口头禅。
在管虎的《老炮儿》中,以官二代小飞为首的年轻混混们飙车、寻乐,以自我为中心,生猛的天不怕地不怕,缺乏对传统和老一辈的尊敬,嘴里经常挂着“他妈的”和“你丫”。

当六爷提出赔偿两千块钱给被划的法拉利补漆时,小飞对六爷说:“老头,你他妈是猴子请来逗逼的吗”,当六爷为找儿子闯入晓波租住的房子,室友黄毛骂道:“你他妈谁呀,孙子,你信不信我抽你”。
在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少年时期的马小军整日上窜下跳,无所事事。瘦弱胆小的他既没有刘忆苦那样的帅气,也没有刘忆苦那样的力量与会打架,只能靠说脏话来维持自己虚假的强大。

在伯明翰学派的理论中,语言作为符号和代码的功能被大肆开掘,多样化的表达方式受到推崇。如今,脏话为青年人提供了特殊的话语空间与批评方式,说脏话已经成为边缘青年特殊的混世方式。
福柯认为话语与权力相互依存,权力通过话语来对人们进行统治。在社会道德危机下,第六代电影中这些浮躁、叛逆、玩世不恭的青年人,或许并没有真正理解污言秽语的含义。

他们只想以你丫这类愤青特有的语言和话语来塑造自身身份、凸显自己的强大,宣泄内心躁动与狂热、在困顿无望的青春里聚众取暖,在“意指实践”中完成对主流话语、社会政治秩序与文化霸权的抗争与反叛。
第六代导演也在影片中应用了脏话这种亚文化语言符号,以反思现代社会问题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原因,彰显自身对主流与权力不屑一顾的态度和对情义丧失、金钱至上的丑陋社会的抨击与鄙视。

嘶吼作为一种肆无忌惮的身体语言,在形式上没有任何的顾忌,与正式、规矩的官方语言具有语言上的差异性,被官方合法语言所抵制和排斥,因此嘶吼也是一种非合法语言,其抵抗、宣泄、边缘的特性也亚文化相契合。
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中,青年人的嘶吼始终洋溢着一种精神,那就是反叛。他们如艾伦·派克《迷墙》中的主人公平克一般,在情绪上步步累积,直至最后歇斯底里般激烈地发泄,在情绪的渲染下,他们的身体姿态也不受形式的束缚,随心所欲的发泄着内心的愤怒、控诉着残酷无情的时代。

在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中,小贵看着即将被抢走的山地车,绝望的用尽全力嘶吼出来,他嘶吼的声音十分尖锐,如一头绝境中的困兽,世界安静的只剩下他一人的嘶吼。
众人被小贵绝望、愤怒的嘶吼吓住了,停止了抢夺,小贵在嘶吼中跌跌撞撞地爬向山地车,把整个身体匍匐在车上,就这样,小贵与众人对峙到深夜。
在滚滚的现代化城市浪潮中,导演以绝望境遇下的嘶吼这个亚文化声音符号,强化了小贵外来者的“他者”形象,展现了其对命运的抗争及抗争的力量感。

在贾樟柯的《站台》中,1984 正值新中国成立 35 周年,经济变革的大潮吹到了汾阳这样封闭偏远的内陆小城,崔明亮、钟萍那群小镇青年也跟着剧团外出走穴,去到了更大的世界。当崔明亮们在河滩里听到远处传来的火车汽笛声时,他们所有人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发疯似地尖叫着、呼喊着向火车跑去。
当他们看到火车呼啸着扬长而去时,奋力的将身体向前倾,拼尽最后一口力气,声嘶力竭的朝着远方尖锐的嘶吼,他们激昂的情绪中透露着些许失落。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火车成为了一种进步的象征,同时也象征着想象中的未来,对崔明亮那群小镇青年来说,火车连接着外面的新奇世界,亦承载着他们的命运和机遇,而他们追逐不上的火车,就像自己抓不住的命运和无法融入的新世界。
在急剧加速的现代生活中,他们始终没有摆脱小镇带来的隔绝与不堪重负之感,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他们焦虑、无助、恐惧,只能任凭青春的嘶吼穿透荒野,以高昂的情绪激发内在力量,嘶吼这个亚文化符号亦代表着小镇青年在理想、追求得不到满足时,在绝望、迷惘中的一次大宣泄。

在张扬的《无人驾驶》中,李欣不会说话也听不见,她强烈渴望自由,希望冲出备受牵制的“牢笼”感受世界。
当里加开着她的小汽车,在夜晚霓虹璀璨的都市里兜风时,李欣激动地把身体探出汽车的天窗,张开双臂感受着“青春的激情与浪漫”,她勇敢的撕掉了缠在身上的束缚,迎着风欢喜若狂的嘶吼着。
导演以游戏式的嘶吼亚文化符号,展现出边缘青年对主流社会“他者化”规训与压制的反抗和对宿命的抗争。

布尔迪厄的社会语言学提倡将语言置入权力话语和社会历史环境之中加以考察,在艰难的从影环境和权力话语的压制下,第六代电影中所呈现的嘶吼这种亚文化语言符号,代表着第六代导演那一代年轻人对整个社会提出的抗议和申诉,以及第六代导演自身对无所不在的专制和主流话语的反叛与抵抗。
20 世纪 90 年代以第六代导演来,从未丧失书写青春的热情,他们的影片呈现出了青春的不堪与痛苦以及青年人所特有的忧伤与寂寥。

当人们逐渐崇拜起商品拜物教,疏离于主流文化的青年个体也在历史虚无感中完成了自己的成长。在喧嚣、浮华、无序的现实世界中,成长的残酷与现实的磨灭就像飞驰的卡车,无情地将他们通通碾碎,成长带给青年人更多的是忧伤、惶恐以及莫名的虚无。
他们的青春无所依靠,充满了迷茫与烦恼,当个体的欲求与客观世界相距甚远时,青年人不得不将自己放逐于社会秩序之外,脏话与嘶吼这种处于主流文化对立面的亚文化,便成为青年人追求个性、彰显自我、宣泄情绪的主要方式。

随着电影艺术逐步大众化、商业化,热衷于呈现社会变革下普通人生活状态的第六代导演也逐渐被边缘化,在中国电影界与市场经济中边缘化的生存处境使得第六代导演的青春天生具有残酷的本质。
语言作为一种符号,是人物行为和意识形态的载体。第六代导演通过脏话与嘶吼这些亚文化语言符号在影片中的呈现,完成了一场对残酷青春的戏谑性自嘲,也象征了第六代导演那无所归依的青春。
#头条群星9月榜#
言承旭真的过气了吗?被赵丽颖粉丝嫌弃,组团狂骂经纪人不作为!
招黑的赵丽颖这回又“惹事儿”了,网传她和言承旭即将出演《你和我的倾城时光》的男女主角,按说原著小说本来就大受追捧,言承旭也是公认的男神级帅哥,演技也不至于尴尬,和志玲姐姐的复合传闻时不时登上热搜榜,惹得全民为他们着急,人气绝对是没话说。可是,谁曾想到这么好的一件事,却惹怒了赵丽颖的粉丝,组团抵制也就罢了,还在微博刷屏骂起了赵丽颖的经纪人。娱乐天地2023-05-25 23:10:160000网传李双江葬礼为不实信息,一家人其乐融融参加聚会
在阅读此文前,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小编将每日为您带来精彩内容,希望您不要错过哦~文|扶汐染编辑|扶汐染最近一条81岁的李双江因病去世,儿子李天一出席其葬礼的消息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但是在这个惊人的谣言之下,李双江夫人梦鸽却站出来愤怒地驳斥谣言,揭露谣言背后的谎言。娱乐天地2023-09-04 16:50:470000主持人梦桐:与富商结婚19年零绯闻,今47岁风韵犹存
文|农人说娱编辑|农人说娱人在这个世间都有自己的目标,有人想要事业成功,而有人想要一生幸福。而在央视工作26年的梦桐不仅是三大花旦之一的主持人,还是失误次数最少的。谁能想到在她报考这个专业时根本就没有接触过,对这个行业更是一窍不通,现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事业美满、家庭幸福的人。她凭借着自己的气质,收获了非常多的观众。娱乐天地2023-12-28 18:50:180000看见71岁朱琳老去的模样,才发现:八十年代大陆第一美女名不虚传
一句媚骨柔情的“御弟哥哥,别来无恙”。让观众记住了倾国倾城的女儿国国王。也让朱琳,走进了所有男人的心巴上。而真正的美人,从来不会被岁月所败。如今71岁的朱琳已然老去,但依旧优雅而美丽。身边的人都已头发花白,可朱琳还是不显老。看了她如今自然老去的模样。谁不感叹一句:不愧是80年代的“大陆第一美女”。然而,拥有这样优秀的基因,朱琳却至今没有一儿半女。娱乐天地2023-10-25 19:12:240000刘晓庆入狱442天,风波过后完美逆袭,骨子里的坚韧让人钦佩
《乘风破浪的姐姐》的热播,让很多人看到了中年女星不一样的风采,也让每个人不禁感叹,三十岁对于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有的人开始通过节目自我反省,有的人开始回想自己曾经的过往,是否应该从现在开始起,做出一个改变。看着别人的人生,做出自己的调整。娱乐天地2023-05-10 00:34:3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