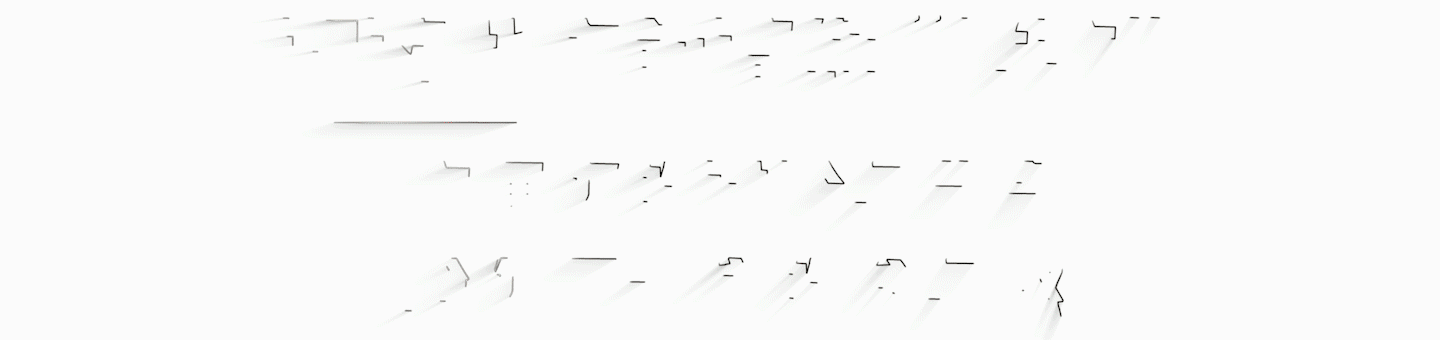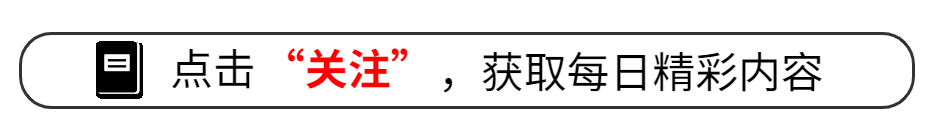翁虹熊乃瑾双星斗艳,为夺黄金设下计中计,最终结果如何?
文丨青琰纪史
编辑丨青琰纪史

这也同时说明内地年轻一代导演的电影观念从某种程度上浸染着香港电影的风格,而随着香港与大陆合拍及营销电影共同市场的建立,成熟的香港商业类型或多或少会成为内地青年导演的效仿和实践对象。
香港电影因为文化身份的特殊在很多题材上拥有内地电影不可比拟的优势,而内地电影最应该吸收的是香港电影对外片本土化的能力。当初《天下无贼》其实遭遇了审查机构的质疑。
有人觉得:影片中对刘德华和刘若英的贼夫妻和以葛优、李冰冰为核心的盗窃组织的描绘,在价值观方面有过分“西化”之嫌,不符合当下中国的文化语境。

幽默的对白,精湛的偷窃技巧,用特技创造出的奇观化的炫技过程,使得这种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人群——贼独具“魅力”,对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为此,制作方对剧作结构与人物关系进行了不小的调整。
戏剧核心由两股偷盗势力在火车上的精彩对决演变成刘德华由惯偷变成“义盗”的过程,最后警察收网,原来两股势力都在警察掌控的恢恢法网中,观众受到动摇的价值观尤其是对“贼”的认同顷刻间回归主流正途。

但此时商业导演已将“盗窃术”和“骗术”的奇观展演成功售出。中国电影进入商业化体制改造的轨道,自然存在商业电影与主流文化传统某种程度的不合拍。当下中国电影肩负着“文以载道”的“悠久”传统,还承载着国家主流价值的传播与维护。
即便有些观众和创作者不这样认为。显然,《双城计中计》充斥其中的“骗”与“偷”,以及与之相关的奇观展现,与当下社会主流价值观显然是相悖的,以“骗”与“偷”为主体的“骗术电影”照理是无法“引领、教育、正面”服务于社会普罗大众的。

于是,影片需要像《天下无贼》等成功商业电影一样对原始文本进行重装与营销。成功商业电影的营销术必须将商品的卖点诉诸芸芸大众的潜意识欲望。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说,商业电影中的“骗术”折射了社会中现实资本的“巧取豪夺”。
这也是“骗术电影”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发端并成熟的原因——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物质欲望遭受到社会资源、法律制度和伦理观念的重重束缚,借助影院的梦机制,芸芸观众的潜意识在影片中的不法之徒身上酣畅淋漓地宣泄。

最后法律和道德适时出现,观众正好从梦中醒来,整理衣襟回家。因此,如今的商业电影,包括像《双城计中计》这样的“骗术电影”,制作者思考的重点不应该停留在片中富有奇观性的负面场景和桥段是否会受到审查机构的警惕。
或对主流价值观构成冒犯,应该进而思考如何成功“包装”这些场景和桥段;换言之,电影的制作者思考的不仅仅是审查问题,更是其后文化层面的经营建构重组问题。
《双城计中计》的故事开端于1924年的上海,孤儿院院长在赌场“出老千”被发现,惨死在黑帮老大林啸天(刘承俊饰)的枪口下。林啸天得知日本人将赠给军阀王大帅(九孔饰)十二箱金子,鼓励其消灭北伐军。

为得到这批金子,林啸天招兵买马,骗术极高的“鬼脸”(任贤齐饰)和“不动石佛”(腾格尔饰)都成了他争取的目标。两位骗界高手参与或不参与劫黄金是通过赌来决定的,进而展开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骗术较量,结局是“不动石佛”认输加入,且各收一徒。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赶往黄金的交易地点:“风口镇”。于是又一场昏天黑地的骗中骗在人迹罕至的西部混乱进行。影片自始至终都是各种骗术的展演,骗中有骗,骗外有骗,单元骗、互动骗,亲友骗、敌我骗,套层骗、连环骗等等,完全是各种骗术叠加的故事。

这种骗术充斥的电影如何成功满足审查要求和社会主流价值的规训,得益于影片剧作和导演提供的符合主流文化价值的“框架保护”。这种框架其实是各种当代与传统伦理价值观的叠加。
其一,故事时空安排在1924年的旧上海与中国西部。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华洋杂处,这样的时空设计为剧作提供了任意驰骋的想象空间。在这样的时空设计中,各种荒诞不经的人物关系和情节安排都可以获得合理性。
更重要的是,旧时代本身的罪恶为银幕上的主人公“行骗”豁免了罪责,使得他们获得了天然的反抗时代罪恶的合伦理性,他们的存在仿佛是罪恶时代的“恶之花”。这是中国电影在展示旧时代下层人民的众生相时常用的一种“框架保护”。

其二,故事在临近剧末时告诉观众:两位江洋大骗是为了替师父报仇而设计了这个大骗局。原来从赌场小混混被林啸天抓住并供出金子财路开始,就是一个骗局。影片倒叙展露了这条深层叙事线。
两个兄弟为孤儿院院长报仇,设计借恶棍林啸天之手,抢断了日本人送给军阀的十二箱金子,捐给了孤儿院,并借军阀之手收拾了恶棍。日本人和军阀也在火拼中两败俱亡。这种复仇动机使得两位主人公的行骗具有无可争辩的合伦理性。

尤其是,他们的师傅是一位受尊敬的乱世孤儿院的院长,他是为孤儿院上赌场,重操旧业被识破而被黑社会夺命的。骗术的合伦理性产生,观众也便原谅自己在不知情时放纵过的对骗子的潜意识认同,舒心地回味骗术的惊险和复杂,并坦然地确认对主人公的认同。
随着故事的开始,观众会自觉地和本能地考察负载着价值的世界和人物的全貌,力求分清善恶、是非以及有价值的事物和无价值的事情。他们会力图找寻“善”的中心。一旦找到了这一核心,情感便会倾向于它。
如同影片《教父》,整个家庭乃至警察、法官都是腐败的。但柯里昂家庭却有一个“善”的素质——忠诚。这使他们区别于其他黑手党,使他们成为“好人”,使观众们的情感倾斜移情于他们。

而《双城计中计》也一样,只要有了为博爱师父复仇的动机,两位乱世大骗子就能轻易赢得观众的心。其三,故事中的两位“大骗子”原本有一个杀害师傅的仇人:黑社会头目,这个仇人本来似乎足以让两位主人公的骗术获取合伦理性。
但影片却为两位主人公增加了一个更重要的敌人:日本人。日本女间谍和日本军队不仅让故事跌宕起伏,而且也为主人公的骗术和伦理性获得更坚实的基础。因为日本侵略者正是大众文化中最易辨识,因而也是影片最容易把观众的认同安排妥帖的形象。

电影中加入日本人,无疑契合了中国近年来对日本怀有的民族主义的一贯情绪。在一系列人物关系中,抵御外族侵略上升成为最主要的矛盾。“抢日本人的钱”也成为“复仇”架构外,更为具象直接的“施骗”纲领,从而将整部影片中的“行骗”提升到某种正义之举的地位。
以上几个主要的保护性框架为“骗术”挂上了多块“护身符”,从根本上把主流价值观难以接受的“偷”与“骗”,转化成为一种“善”举;“小偷”、“骗子”也在合理化的外衣下转换为与不同的恶棍对抗的英雄。

商业电影的这种编剧策略充满了“智慧”,其突破传统文化语境的手段越来越得心应手,值得鼓励。当主人公将历经艰辛截获的十二箱黄金放在教会孤儿院门口时,这种本不符合中国主流价值观的类型电影便在各方面安全着陆了。
“骗术电影”这种外来类型,如果要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生根,除了为电影中非伦理的故事元素寻找合适的保护性框架之外,从现有成功商业电影中汲取各种叙事和造型的元素,唤醒观众的记忆储备,也是令影片能在市场上减少摩擦,实现软着陆不可或缺的手段。

比如,旧上海赌场的场景和细节,无疑借鉴了早已为观众习惯的香港电影中的相关情节。大漠夜店更是充分沿袭了中国西部片的造型元素,连那位女马匪形象,似乎都脱胎于《新龙门客栈》等影片中的人物形象。
有些地方坦白地使用了以往成功商业电影的“典故”,比如对《让子弹飞》中某些台词和情节的戏仿,构成了意外的喜剧效果。
当然影片还直接袭用在市场中已经获得“合格证”的类型电影的类型元素,影片从一开始便深深地吸引住了观众,黑帮片、西部片、赌片、嬉闹片各种类型的元素被充分地运用,这些元素包裹着影片中的各种骗术,客观上成为影片中各种非伦理情节元素的“障眼法”。

这也是多数外来类型电影本土化必须采取的手段。外来电影类型遭遇各种性质的“文化壁垒”,在以往的大陆电影中已经发生过。比如,曾不断有人跃跃欲试,要将“公路片”引进来,结果总是让人失望。
究其原因,撇开“自我成长”中的“自我”观在中国文化中常常“食洋不化”不论,单就“公路片”中浩瀚大地上的小轿车,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多数观众而言,都显得想象力有些“超前”。曾有一部叫《西风烈》的影片,制作者自认为创作了一部大陆市场上“警匪片”的先驱。

但由于中国内地的公共安全系统和社会形态结构与香港、欧美截然不同的特征,最后呈现出来“警不警,匪不匪”式的“隔靴搔痒”感。中国电影的商业化生产目前已渐成规模,但市场上还有很多类型电影未见踪影,好莱坞和香港的类型种类还有好些可以引进吸收。
不过,商业电影体制形成也不可能是电影投资家一厢情愿的事,它必然与现有主流文化构成必然的博弈。而商业电影体制一旦形成与确立,外来的电影类型只要巧妙突破现有的主流文化语境甚至形成共谋,像《双城计中计》这样的类型本土化引进,似乎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外来类型能否为本土化着陆牺牲,改变原有特质,能否更深入地理解本土主流文化形成的历史,仍考验着电影制作者文化创造的能力。这也是像《双城计中计》这样的类型引进仍有可能改进的空间,也是制约着这类影片获得更大社会与商业效益的关键。
帕里斯·希尔顿素颜惊现!与妆后相差天壤之别,肤色暗沉脸型方正
帕里斯·希尔顿:娱乐界巨星的多彩生活在当今娱乐界,帕里斯·希尔顿(PairsHilton)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她不仅仅是一个社交名媛,更是一位商业巨头,一个幸福美满家庭的母亲。她的生活故事如同一部精彩的电影,从素颜曝光到创办化妆品公司,从家族财富到个人时尚品牌,每一个章节都闪耀着她的多才多艺和她在商业帝国中的成功。娱乐天地2023-12-28 17:43:260000她是赵本山的“梦中情人”,曾与陈凯歌相恋,如今59岁过成这样?
说起曾经的央视女主播,几乎人人都能独当一面撑起整个台。但无论是以知性著称的董卿,还是以大气著称的周涛,她们都是倪萍的后来人。倪萍出生于山东,她一开始并不是从事主持人工作,她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曾经演过一段时间的话剧,还是我国二级演员。随后倪萍来到央视,正式在央视工作,她以亲切大方直爽的山东大姐形象迅速走红,并圈了许多粉丝。从1990年开始主持《综艺大观》节目,收视率一直高居不下。娱乐天地2023-05-30 17:50:110000玩弄周润发、包养男友16年,如今56岁的郑裕玲,除了钱一无所有!
她曾是香港影视界的女神,她曾是金像奖、金马奖双料影后,她曾是周润发心中的女人。她就是郑裕玲,一个让无数人羡慕嫉妒恨的女人。但是,她的感情生活却一直不顺遂,从拒绝周润发到包养渣男,她付出了太多太多,却换来了一无所有。如今已经56岁的她,依然孤身一人,没有家庭没有孩子,只有钱陪伴她度过寂寞的晚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个悲惨的故事吧!娱乐天地2023-10-10 12:03:410000喝酒不找黄渤,聚会不喊胡歌,娱乐圈四大“禁忌”你知道几个?
#黄渤##胡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属性,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为人处世之道。而作为娱乐圈里的闪耀明星们,长期暴露在聚光灯下,他(她)们的性格特点、行事风格也被放大、被熟知,不仅被粉丝们“津津乐道”,也成了圈内圈外的”调侃话题”。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娱乐圈内流传的四大“禁忌“,据说,前三个凭借的是个人实力,最后一个却如有天助,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喝酒不找黄渤。娱乐天地2023-05-10 15:59:070000央视最美主持顾永菲:如今已经77岁的她,过的还好吗?
文|L先生编辑|笑史云烟她因《雷雨》这部话剧一夜成名,却因为工作压力自吞300片安眠药。顾永菲,这个名字曾经熟悉无比。1983年的春晚,她与方舒并肩主持,美貌动人,实力超群,一时间成为娱乐圈的炙手可热人物。然而,她两次因感情受挫,在绝望边缘徘徊。受不了压力的她竟然想要吞药结束自己的生命!被抢救了七天七夜,才保住自己的生命。如今已经77岁的她过的还好吗?娱乐天地2023-09-06 01:02:470000

 正在请求数据,请稍候!
正在请求数据,请稍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