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瑞尔的创作理念,在电影中的呈现方式,有何特别之处?

在加瑞尔的创作理念中,演员的表达和创造是电影艺术的重点,他让演员在表演时有思考的自由,以生活的节奏,在影像中呈现自然的身体姿态,用纯粹的身体去感觉,去创造。

影像中演员的身体是复杂和多义的,既有被拍摄被记录的人物角色的身体,也有在运动在表现的演员个人的身体。
演员在表演中,其实是一个多层身体共振的过程,演员身体与角色身体相遇,相互交叉、相互穿透去实现生命力的涌现。
加瑞尔清楚演员无法完全变成角色,他始终在做的,是在帮助实现演员和角色在表演中的内在的融合。

关于如何引导演员进入角色,加瑞尔使用了夏尔·杜兰的方法,这位杰出的法国戏剧革新家,曾创立“演员实验室”为法国剧场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演员。
包括著名的安托南·阿尔托,加瑞尔的父亲也曾是杜兰的学生。在父亲的传授下,杜兰的方法为加瑞尔所用。

因此,演员在表演中不是变成角色,而是用自己的身体连接真实生活和故事人物。在表演的过程里,演员的身体与角色的身体共存。
认为电影中的人物是生活形象的艺术化再现的看法,显然与加瑞尔的创作理念不符。
演员身体和角色身体,不是从属关系,而是有着不同力量的身体的不同层次,没有所谓的主体和客体,不同层次的力量的相互影响。

身体的共振不仅存在于演员表演时的个人内在体验中,还表现在演员和演员之间互动时力量的相遇,加瑞尔将其称为一种“化学反应”。
他有着特别的选角方式:总是把一个演员当做起点,去找另一个适合他的演员。
加瑞尔在罗马遇见安娜·穆格拉利斯,当时正好在寻找《嫉妒》中扮演路易·加瑞尔伴侣的女演员,观察拍摄的一段试戏后,他发现安娜和路易之间的“神奇的化学反应”,于是选择了安娜。

《一日情人》在确定女儿艾斯特·加瑞尔担任主演后,需要从戏剧学院的学生中挑选另一女性主角与她搭档,加瑞尔于是组织剧本阅读,通过演员之间的对白来判断磁场,观察演员之间的互动,艾斯特选择了露易丝·谢维洛特。
《我再也听不见吉他声》同样如此,扮演女主角的约翰娜·特尔·斯蒂格选择了贝努特·里格恩特来扮演男主。
在一般情况下,电影制作流程中对演员的挑选标准,从外貌特征到形象气质,是使演员身体与人物形象达到最大程度的匹配。

这种选择是为更好地塑造人物角色的需要,但归根结底,演员被用来再现人物角色。
加瑞尔从不追求这种“形似”,也不是完全从个人喜好出发进行选择,他最在意的,是身体的共振,存在于演员与角色之间,演员与演员之间。
加瑞尔电影导演身份之外的另一份工作,是在戏剧学院教授表演。他认为表演课的教学有方法,但不是教材,只是记忆,教学或者拍摄时他要做的,不是教导,而是引导。

加瑞尔很少讲戏,而是让演员阅读剧本,熟悉台词,并形成记忆反射,让演员自己去领悟,从中发现一个词可以有双重含义。
拍摄三部曲《嫉妒》《女人的阴影》《一日情人》,有着同样的排演工作,即连续一年每周六进行排演,在反复学习剧本中发现一些他们之前没能领会的新东西,他认为,这才是让演员提高演技的方法。

真实自然的表演,是在演员领悟到要表演的内容、并在自由地思考后给出的反应。
大多数时候,一个镜头只拍一次,即使出现问题需要拍第二次,加瑞尔也不会让摄影机停下来,而是立马就进行下一次的拍摄,出于场地、人员和资金限制。
如今的大部分电影都不会按照剧本顺序拍摄,以最大限度地节约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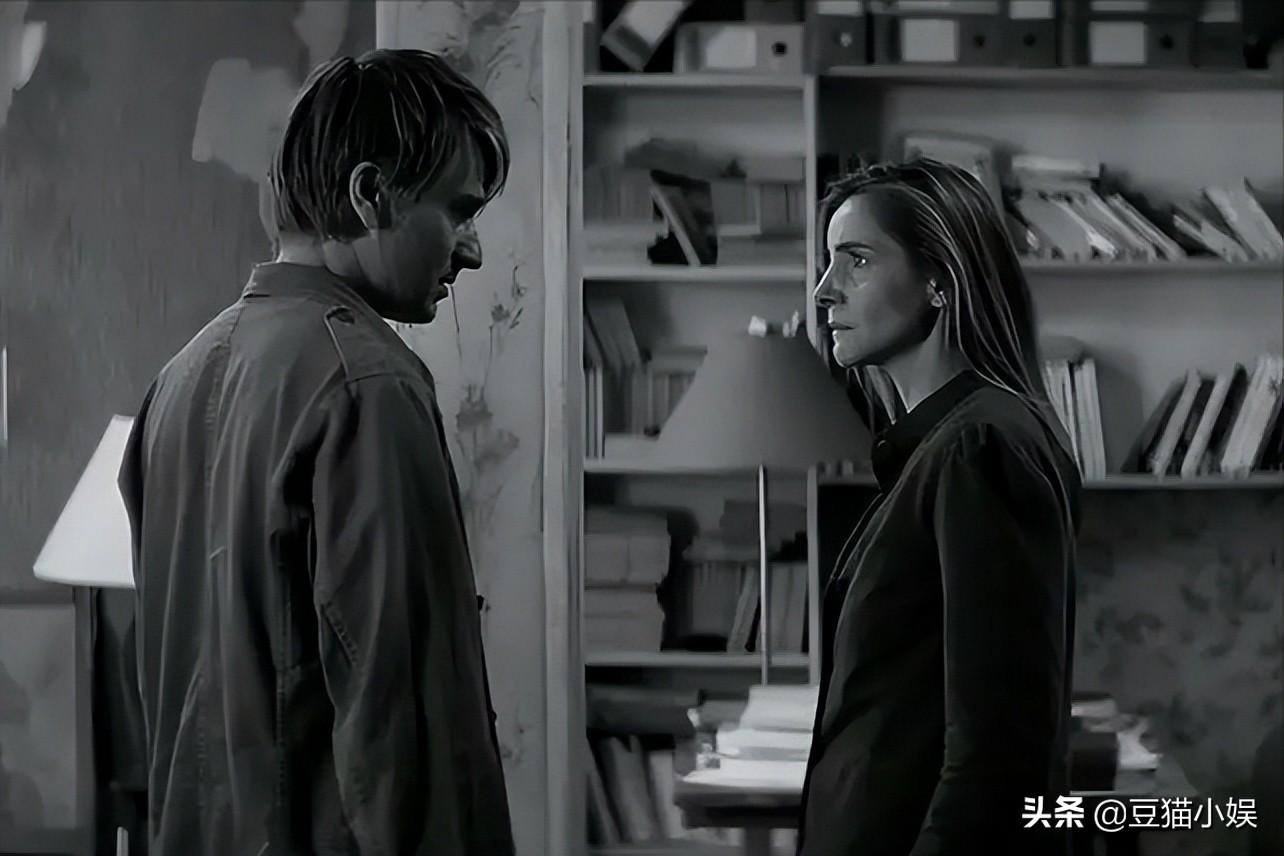
十分注意控制资金预算的加瑞尔,却是为数不多的始终按照剧本的线性时序拍摄的导演之一。
保持演员感觉的连贯性,这样,摄影机在捕捉的演员的状态的变化,与影像中呈现的身体姿态,则有最为真切的身体感觉的连接。

加瑞尔十分注意不去过度剪辑,以保留无意识呈现出来的东西。在有剧本、有意识地表演中,演员会有无意识的自我表露,这些无意识生发于身体的偶然,极其珍贵。

加瑞尔把影像的重点更多地放在人物的感觉上,人物的姿势和动作不是为了解释或者导致因果联系,而是处于一种悬置状态。
他在影像艺术的表达中选择了身体,身体给予感觉又接受感觉,而影像捕捉身体又呈现身体,生成无限的感觉的层次。
之前和之后,自我和他者,内在和表层,贯穿于影像生成的过程中。

身体不是叙事工具,不是为了讲述什么、告知什么的存在,而是生命力的实在的具体化身,加瑞尔正是用身体的姿态向我们展现生命的力量。
加瑞尔在电影中直观地呈现了大量的身体的悬置状态,此时的身体不指向任何意义,不为任何故事情节服务,而只是一种身体感觉的自然流露。
早期的非叙事电影是加瑞尔对这种悬置的身体姿势的极端演绎。

八十多分钟的长片《高度孤独》没有讲述任何故事,固定镜头对准演员的脸,躺在床上的身体,有时自我沉睡,有时挣扎有时沉睡,有时盯向镜头的方向,微笑的表情,痛苦的姿势,疲惫的身体,大量的面部大特写。
相比于《高度孤独》捕捉更多的面部表情,《各种起源的蓝色》则主要是对身体动作的捕捉,同样是固定镜头,但更多的是中景,穿插少量的特写和全景,徘徊的身体,等待的身体,望向远方的姿势,站立的或者斜躺的姿势,阅读、写作、交谈,看相册的姿势、弹钢琴的姿势……

《水晶摇篮》同样是一部展示身体姿势的电影,没有故事,没有话语,只是人物的表情、姿势组成一个个镜头的接续。
大量的停顿、迟疑同样出现在加瑞尔的叙事电影中。
《秘密的孩子》用二十多秒的固定镜头给一张坐在地上的摇滚女孩的照片,在躺着的女孩和坐着的男孩间摇移,女孩望向男孩,男孩看一眼女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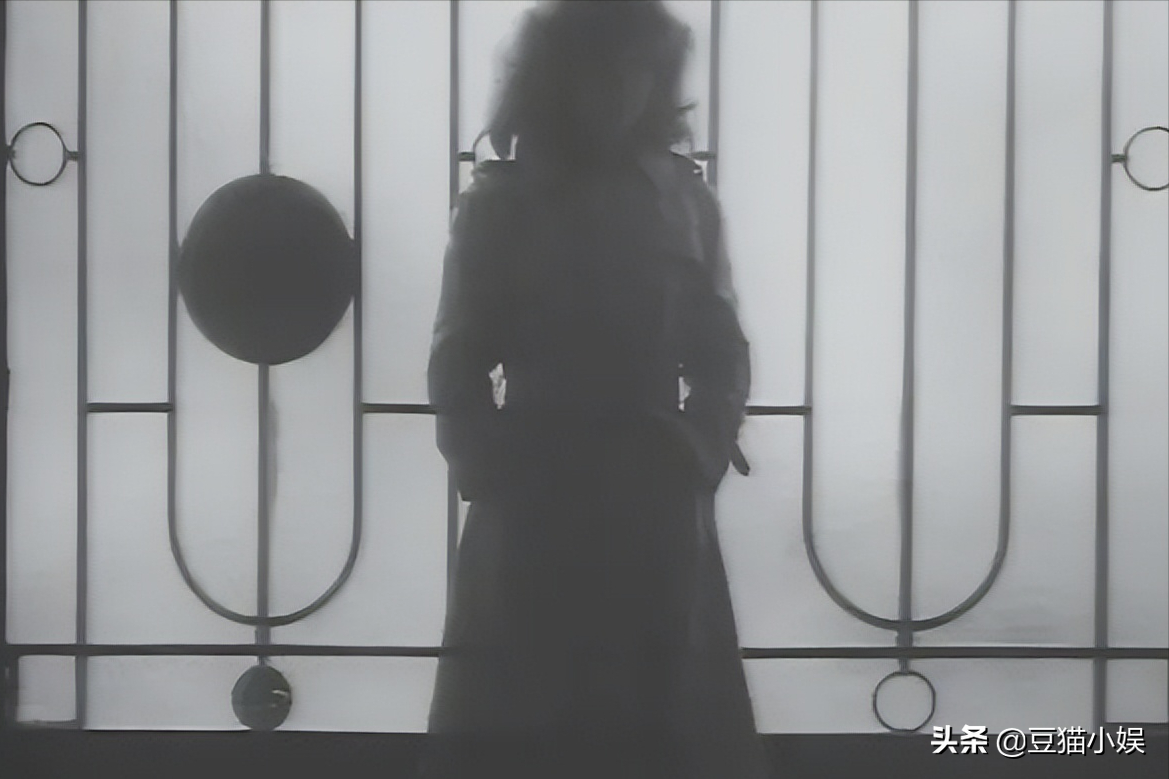
在另一个镜头里,二十秒的时间呈现一个躺在床上的女人的脸,接着切换到女人的背影,同一室内靠窗而坐的男人双手触碰着头,似乎很沉重,接着切换到女人的侧脸,在画面的右下方,漫长的段落里没有言语,仅仅是身体的姿势,一种姿势到另一种姿势,没有任何解释。
《自由,夜》女人独自一人坐在空荡的剧院缝缝补补,断断续续传来抽泣声,这个段落长达三分多钟,由两个镜头组成。
全景镜头展现诺大的光线模糊的剧院,中景镜头让我们看到女人低垂的面庞和手中的针线活,女人抽泣的动作被清晰呈现。

《我再也听不见吉他声》以25秒的时间展现睡着的女人为开始,女人的姿势被刻意凸显,回到家后靠墙而坐的几乎静止的姿势,看着某处的缓缓移动的眼神。
睡觉的姿势,疲惫的姿势,行走的姿势,身体的姿势在水平空间中被拉长,在特写镜头里被放大,在漫长的影像之中被凸显。

加瑞尔对舞蹈似乎有着一种偏爱,他的影片中常常会出现舞蹈的场景,时长几乎达到一首歌的时间,非戏剧性的场面,没有复杂的叙事进程,仅仅是身体的运动、身体的交错、身体的互动,这是极为真诚的身体的记录。
在加瑞尔营造的舞蹈场景里,身体的动作没有固定的模式,身体运动的向度在舞蹈中得到极大的拓展,身体的姿势和变化充满了不确定性。自由的舞蹈,是身体自身的自然运动本性的充分流露。

十五分钟的短片《失谐的孩子》是加瑞尔真正创作影像的开始,长达一分多钟的舞蹈,是这部短片的一个亮点。
男孩把他的录音机放在耳边,欢快的音乐响起,画面切换到两人的舞蹈,男孩和女孩紧贴着的身体缓缓摇摆,在空旷的房间里迈着步子,手持镜头也随之运动。
在后来的作品中,舞蹈场面更加开阔,通常是一场众多年轻男女参与其中的舞会,陌生化的身体和陌生化的运动,身体的相遇表现出一种随机性,每一种姿势、每一次碰撞都难以被准确预料,而是向着无限的可能。

《狂野天真》有一场戏中戏的舞蹈,随着音乐渐近,人物缓步行走,然后切换到近景的两个人的舞蹈,杯盏交错间,身体的姿势柔缓而优美;
《平凡情人》里一群朋友在聚会时欢快地跃动,不同的身体纠缠和分离,欢快的气息里夹杂着浓烈的颓然;

《炎炎夏日》中近四分钟的舞蹈场景,近景镜头对准莫妮卡·贝鲁奇的身体。
随着音乐节奏独自进入画面的背影逐渐明晰,接着与舞池里的不同身体相遇和互动,最后靠近一个陌生男人,双手合十、伸展、拥抱、分开、亲吻、抚摸,既陌生又亲密的暧昧气息在无需言语的身体交错间弥漫。
《一日情人》里女儿珍妮和父亲的情人阿丽亚娜一同参加舞会,各自和陌生的身体跳舞和交谈,三分多钟的舞蹈在黑白影像间流露出悠然和哀伤。

《眼泪之盐》的舞蹈场景也近三分钟,男主卢克与朋友及新认识的女孩贝茜去跳舞,舞蹈呈现身体的碰撞和交汇,光线变化下的身体时而明晰时而晦暗,相遇——行走和交谈——舞蹈。
谢谢观赏,关注我,了解更多精彩。
越老越帅的男星我只服这4位,不整容,干净清爽,连褶子都是魅力
文|小y编辑|小y这段时间,杨洋的事闹得沸沸扬扬,明明长了一张帅脸,却被嘲讽是油腻男的接班人。正值青壮年,可他的脸上却出现了不符合他这个年龄的油腻感,真是让人尴尬至极。要说帅气在娱乐圈可是最不缺的东西,颜值加自大会让人嫌弃,而颜值如果加上实力,那才让人信服。这几位男明星,虽然年纪大,但是却越来越有魅力。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都是谁吧。娱乐天地2023-08-29 11:07:250001天鹅颈露出来!一组刘诗诗今年的靓丽穿搭造型,美不美?
这次来欣赏一下刘诗诗在2023年里的一些穿搭造型,都很好漂亮呀!2023年2月24日,2023秋冬米兰时装周,身穿Tod’s2023春夏系列的红色皮大衣亮相Tod’s秀场。Tod’s:意大利品牌,DorinoDellaValle创立于1970年。2023年3月13日,《时尚芭莎》2023年4月刊,穿的印花露肩连衣裙来自AlexanderMcQueen2023春夏系列。娱乐天地2023-12-28 12:47:330001你还记得她吗?她曾是央视最红的主持人,如今过着普通老太太生活
如果您喜欢这篇作品,欢迎点击右上方“关注”。感谢您的鼓励与支持,希望能给您带来舒适的阅读体验。退休应该是每个年纪渐长的人都绕不开的话题。即便是以前央视主持人界的担当刘璐。如今年近七十的刘璐已经从央视退休快十年了,偶有观众遇到她。她和所有老太太一样,过着平凡的日子:买菜、做饭、去公园遛弯儿。也许有一天在菜市场或是公园见到和蔼可亲的她。都会忘记她曾经也是家喻户晓的央视主持人。娱乐天地2023-09-29 20:33:160000“性张力”才是叔圈的利器,不露骨不下流,只靠眼神就氛围感拉满
文|史谭a编辑|史谭a影视圈中的演员除了小鲜肉外,大叔们也是别有风味,一举一动皆是男性荷尔蒙。身材俱佳,演技炉火纯青,充满着诱惑迷人的性张力,与女演员的对手戏更是令人心跳加速,面红耳赤。那么就来盘点一下这些叔圈代表让人欲罢不能的片段吧!说起性张力,很多人对其都会有一个刻板的看法,那就是性感,赤裸上身,有很多的腹肌,其实这种看法是十分片面的,性张力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娱乐天地2023-12-15 10:59:170000陈法蓉携年迈老父亲游桂林,57岁仍旧貌美如花,父女俩同框似爷孙
图文/德里说娱乐编辑/德里说娱乐前言这个关于体育项目的故事并非聚焦于场上运动员的艰苦拼搏,而是聚焦于一位年过半百的女性,她虽非职业选手,却以坚持健身的态度令人刮目相看。57岁的陈法蓉,以貌美如花的容颜和坚韧的意志令人印象深刻。娱乐天地2024-01-03 13:06:000000







